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上次写完了那篇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 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妄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这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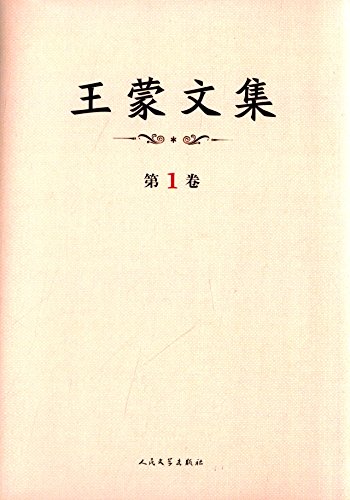 这个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阴损,缺乏绅士风度。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认同的:即李达派蛮不讲理,或者还自以为有什么来头,或者还一心要扫除一切把逵字不读做达的人。不应该是权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结果当然只能是害了自己。这个故事对于振振有词坚持谬误,由于过于强硬搞得没有人愿意把事实真象告诉给他的人,还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义的。这个故事的最大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喏喏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
这个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阴损,缺乏绅士风度。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认同的:即李达派蛮不讲理,或者还自以为有什么来头,或者还一心要扫除一切把逵字不读做达的人。不应该是权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结果当然只能是害了自己。这个故事对于振振有词坚持谬误,由于过于强硬搞得没有人愿意把事实真象告诉给他的人,还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义的。这个故事的最大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喏喏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
我也想起了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实质上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胡适的这个主张被认为是反动那是当然的,因为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当时的政府而不利于当时一心想革命造反的共产党和人民。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呢?这事就得另说了。革命成功了,您还是整天价主义,整天价为标签而不是为实际,为“社会主义的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苗”而大动干戈,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恐怕就要自乱阵脚。主义与问题本来也是分不开的,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根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对于革命政党和人民来说这就是政权问题。政权问题解决了,各种实际问题就有了好好解决的条件了。只要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掌权,而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夺取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把目光放到多谈些问题上来。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能更好得多地解决问题,能满足人民的实际利益要求最终,人民是务实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一个主义,并不在于这种旗帜本身,并不在于某种学说的论断、逻辑与文采;而在于这种主义和标榜这种主义的政权是不是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切身的实际问题。
提到不争论云云,老子的学说很有片面的深刻性与启发性。从反对人的盲目自大、盲目膨胀、庸人自扰、轻举妄动、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的意义上来理解,老子的学说实在精彩绝伦。他推崇“不争之德”“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他提出“希言自然”等,我们不妨理解为不必自以为是地不适当地以喋喋不休的言语去干扰事物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说不定从中可以悟出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道理来。老子还发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至高至妙的道理。我们不妨认为,老子的主张是韬光养晦,不做出头椽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子的主张也是高姿态,是对于自己的充分自信。耽于争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结果;例如文坛上一些动辄要争一争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尽的过气作家而已,即使争到了一些蝇头小利,暴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极端鄙俗,极端心虚。而一个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是不屑于争那些个低级趣味的。为什么不争?一是不必,胸有成竹,不战而胜,是为上上。二是不屑,与四七二十七者争论,不是太降低了自己么?三是没有时间,好人忙于建设,忙于创造,哪有空闲天天磨嘴皮子?以其不争,更显示了他的高尚与宽宏。对于不争的人,你能胜过他吗?你至多吹嘘一番为自己壮壮胆罢了。你至多讹讹搅充当一两次搅屎棍罢了,不是只能越发显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还是够不着么?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旧前进”的含意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张骆驼队应该与狗争论。老子又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不认为这是老子主张大家都应该躺倒睡大觉,同样,他主张的是更实在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做逆客观规律而动的事情。
老子提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俗话里也有“言多语失”、“爱叫唤的猫不拿耗子”之类。消极地看,这一类说法似乎是教给人谨小慎微。其实,个中自有深刻的道理。依我们的经验,凡是要大喊大叫地说是“就是好就是好”的,常常是搞得不太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唱过“淮海战役就是好”“改革开放就是好”,却要不停地唱什么公社就是好或者文革就是好,这还不清楚么?所以懂得了“多言数穷”的道理,一是有助于不上当,二是有助于少做蠢事。话语确是人类的一大发明,话语的转而君临人世、安慰你梳理你的同时蒙骗你煽动你辖制你镇唬你,也堪说是人类的一大灾难。老子早就对于话语的泛滥采取警惕和疑惑、批评的态度,实乃东方一大智者。
老子的名言还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他总结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不妨将这些教训理解为,直面人生,不为天花乱坠的话的力量所蒙蔽。多做实事,坚持重在建设与正面阐释,尽最大力量避免抽象无益不看对象的争论。(这里的“善”的含意与其说是善人,不如说是聪明——善于做某事。)警惕那些卖弄博学的驳杂不纯者,只有那些不但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且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才有起码的知识。不必处心积虑为一己打算,“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固本自强,完全不必争一日之短长——尽量避免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排他性、狭隘性和破坏性。这些都是金玉良言。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次便是真理。比如红海洋与背诵“老三篇”,动不动搞什么复盖版面;还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文革当中,既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示了话的力量——威武雄壮,移山倒海,蔚为大观,是话的力量的一次大示威大节日大活剧;又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现了仅仅是话的力量的不足恃,是空前绝后、势如破竹的话的力量的终于破产。这是以话的力量兴风作浪的一出大悲剧;又是话的力量出尽洋相终于成为笑柄的一出闹剧喜剧。可惜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善于接受历史的教训,至今仍有一有机会就致力于搞大批判班子的,情结于用话的力量吓唬人的文革思路迷恋者。
资本主义市场的广告的恶性泛滥也是一种话的力量的异化与膨胀。广告化的市场经济,广告化的政治,广告化的文艺,什么都靠包装,靠“炒热”,靠“托儿”。这些都可能奏效于一时,但是恐怕不可能从而成了什么气候。有时候吹的肥皂泡愈大愈五颜六色愈是接近于噗地一下子破灭。这样的例子难道我们见得还少么?
市场广告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所谓大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与通过金钱来占领传播媒介大登广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造云云,更给人以颠倒本末、推销伪劣的感觉。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舆论首先是实际的反映,是民意的反映,一切的大造如果符合实际符合民意,那将是一种正确的与必要的信息服务,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把好东西贡献或推销出去。而如果产品伪劣,大造舆论也罢,大登广告也罢,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与有限的,最终,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培植出一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且使人民群众更加疏离。
我这里还想斗胆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正确地与全面地理解了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了呢?窃以为,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是宏观性的,是针对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团主义的。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常说的所谓“灌”的教育方法,单向地念念有词地把自己当做话源、话的主体而把受教育者视做话的接受器、话的客体,那会总是有效的么?如果只管这样“灌”下去,我们又怎么样理解毛泽东主席在“古田会议”提出的教育上不要搞“注入式”而要搞“启发式”的命题呢?
余才疏学浅。我十分希望有学长学友能把古今中外的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故事拿出来让人们见识见识。
原载《读书》1994年第6期。
1 Comment
Leave a Reply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说得实在。
《马太福音27:46》(耶稣的死)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 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后世逻辑家据此认定上帝与耶稣并非三位一体。唯俗世凡间并非依据逻辑运转,往世天国虚无缥缈。形而上大多只能一笑了之。是否就了然于心?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