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争录 | 同性恋者不适合做父母?一项被两百学者联名反对的研究背后
学术论争录 | 同性恋者不适合做父母?一项被两百学者联名反对的研究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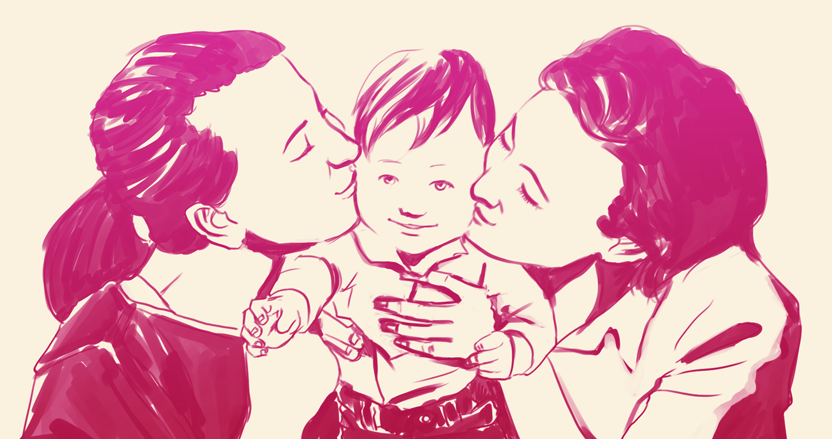
在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辩论中,有人提出:同性家庭养育的儿童在身心健康方面会受到负面影响。
与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同,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界的共识是:没有证据表明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儿童与异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存在显著差异。2005年,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发布了 一份报告 ,回顾了相关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最后清楚地总结道,“并无证据显示同性恋者不适合做父母,或其子女相比异性恋者的子女会受到负面影响。没有一项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子女在任何方面弱于异性恋者的子女。”
然而,2012年6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 Mark Regnerus 在《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研究,高调宣称:同性恋家庭养育的子女可能在若干方面处于劣势。该研究引发了轩然大波,两百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拒绝承认Regnerus的研究结论;Regnerus所在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发表了 一份声明 ,表示虽然支持Rogenerus作为学者进行独立研究,但并不赞同其观点。
那么,Regnerus的研究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又为何会人人喊打呢?
同性恋家庭的子女是“次最优”?
根据美国婚姻与家庭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Research)在2010年的估算,美国约有58万个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其中约98600个家庭抚养了小孩。这个数字看似庞大,但放到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中可谓沧海一粟,很难准确定位。加之同性恋在社会中仍然遭受着歧视和压力,愿意接受调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早期关于同性恋家庭的研究通常需要采用非随机抽样,样本数量也较少,很难将结论推广到一般人群。
Regnerus从这一点入手,声称自己采用了随机抽样方法,样本量也更大,因而结论更为可信。他所使用的数据叫做新家庭结构调查(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NFSS),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人口研究中心主持收集,在18-39岁的美国居民中随机抽样。当然,NFSS的数据中,真正成长在同性恋家庭中的人也很少。于是,Regnerus做了一点变通——他问了所有受调查者一个问题:“从出生到十八岁,你的父亲或母亲是否曾经与同性有过浪漫关系?”他以此来定义受调查者是否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根据这个问题,Regnerus调整了受访者入选的比重,最后共有2988人被纳入研究中,其中父母有过同性恋经历的有236人。
Regnerus 将受调查者的家庭结构分成了八个类别:异性父母双全(919人);母亲曾有过同性恋关系(163人);父亲曾有过同性恋关系(73人);两岁前被父母收养(101人);有继父或继母(394人);单亲家庭(816人);父母在孩子18岁后离异(116人);其他(406人)。显然,在现实中,这八个类别会互相重叠。于是,为了提高同性恋家庭在样本中的比例,但凡父母有过同性恋经历的人,都被Regnerus放进了第二类或第三类,哪怕他们同时符合其他几类的情况也不例外。
Regnerus进而选出了40个指标,包括受访者在职业、家庭、婚姻、心理健康、公共事务参与等各方面的表现。他发现,在排除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影响之后,父母亲有过同性恋经历的人,在某些指标上的确与传统异性恋家庭中成长的人有所差异;特别是母亲有过女同性恋经历的人,其家庭和自身都更有可能需要公共援助,平均教育水平更低,失业可能性更高,更有可能出轨和遭受性侵犯,性伴侣的数量更多……父亲有过男同性恋经历的人也有类似表现,只是呈现出差异的指标数量少一些。可以说,相比起传统异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表现较为负面。Regnerus用了一个看似政治正确的词——次最优(suboptimal)。
这一研究引发了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声称同性恋家庭可能影响儿童成长的研究非常罕见,因此几乎每一个保守派团体都为Regnerus的发现欢欣鼓舞,并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背书。后来,在路易斯安那州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庭辩论中,Regnerus曾被邀请出具意见书。2014年,在联邦法庭对密歇根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进行辩论时,Regnerus亦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但其证言因广受争议的方法论问题而被法官拒绝采信。
发表流程:快得吓人
可以想见,Regnerus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引发了极大争议。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学者 Gary Gates 的发起下,两百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领域学者署名发布了 一封公开信 ,指出Regnerus的文章在发表过程中有若干违反常理之处,可能存在利益牵涉。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类期刊的审稿速度是非常慢的,一篇文章审一年也不奇怪。但Regnerus这篇文章2月1日提交一稿,2月29日提交修改稿,3月12日就通过了终稿!这意味着论文在五周之内就通过了编辑和审稿人的两轮审读并完成了修改过程;而就在同一期刊物中,其他论文的平均审稿期长达一年,中位数也在十个月以上,唯有此文受到特殊优待,实在不太正常。
更值得注意的是,Regnerus的研究由著名保守派智库威瑟斯庞研究所(Witherspoon Institute)资助。该智库有天主教会背景,长期公开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合法化。研究发表后,该智库很快将其当作反对同性婚姻的主要证据,而当时恰好是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
在学术界的广泛质疑下,《社会科学研究》对Regnerus论文的发表流程进行了内部审查。编委会成员、南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 Darren E. Sherkat 独立进行了这次调查, 结果 发布在同年11月份的《社会科学研究》上。Shekat 认为,该论文在发表过程中“违反了编辑程序和伦理标准”。
Shekat指出,期刊找到的论文审稿人中有三位是出名的保守派,一直公开反对同性婚姻;两人曾为Regnerus的研究提供付费咨询,两人曾与Regnerus合作发表过论文。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审稿规定,这些潜在的利益冲突本应使他们失去审稿资格。或许正因意识形态与利益上的一拍即合,审稿人显然并没有认真完成义务,以至于无视了论文中的诸多错误和疏漏。
Shekat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期刊可能出于吸引公众注意和提高影响因子的目的而刻意加快了审稿与发表流程。事实上,这篇论文在发表一周之后就成为了该期刊网站上下载次数最多的文章。然而Shekat的结论是:这篇论文“原本不应该被发表”。在后来的 一次采访 中,Shekat干脆将Regnerus的论文形容为”狗屁不通”(Bullshit)。
数据处理与分析中的错误
除了发表流程中的问题之外,学者们的公开信还指出了论文的一个重要缺陷:Regnerus有意识地将受访者优先分入“同性恋父母”组别而忽略了与其他组别重叠的可能,因此该研究根本无法区分同性恋父母的影响和继父母、单亲家庭或父母离异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Regnerus的分组方式让他无法区分“家庭稳定性”和“家庭结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
2013年,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和马里兰大学的三名学者发表了对Regnerus的正式回应文章,进一步对Regnerus的分析做出了批评。他们指出,该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对“同性恋家庭”的定义——显然,“父亲与母亲有过同性恋经历”和“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重叠度可能很小。事实也证明,Regnerus的数据中,绝大部分“父亲或母亲有过同性恋经历”的个体都不是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的。Regnerus宣称自己关注的是在同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儿童,但他的研究对象却根本不符合这一定义。其实,Regnerus收集的数据更适合用来比较“父/母曾与同性出轨”和“父/母曾与异性出轨”的群体。
退一步说,就算在不严谨的定义和分类之下,Regnerus发现了“父母亲有过同性恋经历”的个体在某些指标上处于下风,这种相关性也可能有许多外部原因。例如,拉拉家庭很可能因为男女在劳动市场上的不平等而在经济方面处于劣势,但这决不能说是女同性恋者的错。类似地,在社会偏见和法律限制之下,同性恋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原本便处于弱势,家庭的不稳定性也因此更高。将这一现实所导致的问题归咎于同性恋者本身,无疑是一种“责备受害者”的逻辑。
事实上,Regnerus的研究反倒能够为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理据——父母亲是同性恋却无法与伴侣结婚,可能是导致儿童受到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通过婚姻合法化来稳固同性家庭,反而有利于提高儿童福祉。然而,对于这些可能,Regnerus全部讳而不谈,仅仅提出一个似是而非且并无理论支持的解释——非血亲父母可能对儿童的关注不够。这也令人怀疑Regnerus作为天主教徒是否让信仰干涉了学术研究。
有趣的是,研究者分析同样一份数据之后发现,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如果父亲或母亲曾有过同性恋经历,那么他们后来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反而更高。
研究者还指出,该研究的样本选择存在重要缺陷:首先,受访者可能有回忆偏差,例如童年经历不愉快的人更可能将其归咎于父母的外遇,也因此更可能回想起父母与同性的关系;此外,由于受访者参加该研究能够获得物质补贴,因此有经济需要的受访者更可能会故意声称父母有同性恋经历,以提高入选的机会。最后,研究者还发现了Regnerus的若干小错误,例如对缺失数据的统计前后矛盾,表格中的小数点错位,以及未能排除明显的极端数据等。这些低级错误的存在也进一步印证了由于审稿周期过短,审稿人和编辑很可能未能充分全面地审读论文就匆忙发表了。
原始数据中的疏漏
Regnerus的论文发表三年之后,其争议仍有余波。当论文的原始数据公开后,其他研究者陆续发现了更多问题。今年三月,康涅狄格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两名社会学家在《社会科学研究》再次发表批评文章,使用同样的原始数据,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两位研究者首先指出,Regnerus的数据编码存在很大问题:在他归类为“由同性恋父母抚养长大”的236个受访者中,超过一半从未跟父母的同性伴侣一同生活过,三分之一从未与有同性恋经历的父母一同生活过;另外53人与有同性恋经历的父母共同生活不到一年。将这些情况归类为“同性恋家庭抚养长大”,实在很难令人信服。
另外,Regnerus将“家庭是否接受公共援助”作为衡量结果的指标之一,这一决定也很奇怪。更合理的做法显然是将其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而加以控制,之后再比较其他指标才对。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了更多不合理或不可能的案例,例如有人声称自己一岁时就被逮捕过。由于原本归类为同性恋家庭的案例就不多,这些真实性不高的极端数据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分析结果。在排除了错误数据之后,他们发现:在所有236名被归类为“由同性恋者抚养长大”的受访者中,仅有51人真正可能曾与同性恋父母及其同性伴侣共同生活一年以上。
将这51人与异性恋双亲抚养长大的群体比较之后,研究者发现,Regnerus所声称的差异几乎全部消失了。仅存的四项指标差异分别是: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否接受公共援助;在家庭中是否有安全感;是否自我认同为异性恋;目前是否与同性有浪漫关系。其中,前两者并不是结果,而是应该控制的因素;后两者则无所谓优劣,也很可能是因为父母有同性恋经历,子女才更容易了解自己的性取向。如此一来,Regnerus所谓的“次最优”就完全不成立了。
Regnerus的研究的确吸引眼球,至今仍被保守团体当作反对同性婚姻的重要理据,其结论也时常被夸大和扭曲。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并不靠点击量来决定,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共识也未曾改变。2013年,美国社会学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供了 一份意见书 ,综合相关文献并着重反驳了Regnerus的研究,最后重申结论: “社会科学界的共识确凿无疑:同性父母与异性父母养育的儿童并无差异。”
参考文献
- Cheng, S., & Powell, B. (2015).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ivergent patterns: Re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ame-sex paren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2 , 615-626.
- Perrin, A. J., Cohen, P. N., & Caren, N. (2013). Are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d same-sex relationships disadvantaged?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no-differences hypothesis.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Mental Health, 17 (3), 327-336.
- Regnerus, M. (2012).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4), 752-770.
- Sherkat, D. E. (2012). The editorial process and politicized scholarship: Monday morning editorial quarterbacking and a call for scientific vigil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6), 1346-1349.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