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杨绛教授正名
请为杨绛教授正名
本文原载于知乎专栏“女权说”(https://zhuanlan.zhihu.com/gender),由作者授权转载
王笑哲 / 政见特约作者
杨绛教授离世,各大媒体纷纷推出相关悼文、讣告。阅览过其中十之八九后,我惊讶于各方对《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杨教授晚年的散文式回忆作品的突出刻画。似乎是迫于钱钟书先生的成就,世人大多无法脱离杨教授“贤妻才女”的身份象征,一边消费着杨钱二位智者遗留于各式轶闻中的饱经世历的感情羁绊——可惜所谓的《百岁感言》并不出自杨教授之手,一边自我矛盾地为杨教授在私人空间中的 “母亲 X 妻子” 形象寻求着超越 “家庭关系” 的表述。然而除去类似萧宜(《干校六记》只许在 “柜台底下卖”)、徐泓(送别杨绛先生)两位老师的个人回忆式的悼文,我只能在平铺式的讣告中(作家、翻译家杨绛去世)寻找对杨教授真实人生的还原。朋友圈的刷屏、媒体的见机行事、公众对 “相濡以沫共患难” 的臆测,这些景观的背后,或多或少被自古以来社会对 “贤伉俪” 的想象所束缚,以至我们无法将视线转移至杨教授作为独立的、自主的智者之生平。
在广泛传阅的各类推送中,“缪斯夫人” 的文章(106 岁杨绛仙逝,“我们仨” 天上团圆 | 重新定义贤妻 )算是别有心裁,从杨钱二位的感情生活切入,旨在推翻传统价值观中对 “贤妻” 的认知,将 “贤” 重新定义为 “既有趣又平等且自由” 的品质体现。然而,文中对 “平等” 的描述并未脱离传统两性的关系框架,如谈及钱先生为人 “呆大”、“打翻墨水” 的桥段时(这段情节真是百用不怠),文章仍是延续了大众媒体对钱钟书 “学人易痴” 的豁免态度,将钱杨二位的家务付出不平等这一事包装为可以理解的、学人之间的感情付出。又比如谈及钱先生的 “誉妻癖”,文章所举的三个例子将杨教授的 “沉着” 皆归为 “在外经受风浪、在家操持品性” 的叙述模式,似乎女性之 “贤” 的落脚点总需回归到私人空间的身姿。
我并不打算提出一种 “杨钱二人夫妻关系不平等” 的批判性观点,我只想挑战主流叙事对 “杰出女性” 的纪念方式。“贤妻才女” 也好、钱先生之 “我做坏事” 的轶闻也好,我们对杨绛教授的尊敬与缅怀若仅仅止于她的《我们仨》——好比木心在公众视野突然的出现发生于《从前慢》;社会对郑念的褒扬离不开《上海生死劫》中所谓的 “高贵、优雅” 的单一式榨取——那么我们将陷入一种伪文艺风格的自我感动的怪圈。这于历史、于杨绛教授、于钱钟书先生、都是不公平的。具体如何为杨绛教授正名,虽然我个人并无十足把握,但或许可以从公共空间的视角着手——而非私人空间中的 “钱夫人” 形象——还原并力推杨绛教授作为作家、翻译家、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人格。
我只读过杨教授的戏剧,不敢对其译品如《堂吉可德》、小说如《洗澡》、散文集如《干校六记》发表意见。这里只谈一谈杨教授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杰出遗产。
杨绛教授作为现代作家,离不开至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其人的推崇。耿德华(Edward M. Gunn)受此启发,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中专为杨绛献出一节,将杨教授与张爱玲、钱钟书与吴兴华同列为四十年代初中国现实主义的表现先锋,评价道:“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杨绛的喜剧,钱钟书的散文和小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排斥浪漫主义作家的装腔作势和价值观念做出了贡献”。[1]耿德华对杨绛的赞誉,与杨绛撰写其传世杰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柯灵称此二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 “喜剧双壁”)的历史背景(所谓 “八年沦陷区” 的文学境域)关系密切。在当年,不同于《碧血花》、《杏花春雨江南》等主流历史戏剧与市民戏剧,杨绛的 “世态人情喜剧”(Comedy of Manners – 又译风俗剧)并不仅仅专注于单调片面的 “爱国宣传”,而是转向对 “孤岛上海” 的道德陷落的批判。以《称心如意》为例,故事主线围绕主人公李君玉寄人篱下的悲喜遭遇,将若干副四十年代初的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画像巧妙地交织成一出反讽喜剧。大舅夫妇针对“录用女秘书还是男秘书”的明争暗斗、二舅夫妇的崇洋媚外、四舅夫妇的家庭纷争、赵家人对徐舅父财产的妄想、赵祖贻与钱寿民的 “中西孰优” 的争辩等等,杨教授以李君玉的辗转为线索,串联起各家气象。作者对幽默的把握是多层次的。《称心如意》有一段是赵夫妇与陈彬如的 “三人小品”,台词穿插之间,人物性格饱满,各自神态十足(此段中懋夫人误以为丈夫在外有了别的孩子,正巧李君玉的男朋友陈彬如入场,引发误会):
【仆人领陈彬如上,仆人下。】
陈彬如: 赵先生?赵太太?
懋夫人: (打量陈彬如)我是赵太太,你是谁?
陈彬如: 我姓陈……
懋夫人: 哦!姓陈——我问你,陈兰贞是你的谁?
陈彬如: 陈兰贞?(摇头)
赵祖懋: 他哪知道什么兰贞!(向陈彬如)陈先生,有什么事?
懋夫人: 我会问他,不用你挡在头里。
赵祖懋: 他找你吗?
懋夫人: 他敢找我!可是得让他知道,我赵太太也有在家的日子!我赵太太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赵祖懋: 你认得他?
懋夫人: 怎么不认得!陈兰贞的兄弟!——不也姓陈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陈彬如: 赵太太认错了人吧?我不认识陈兰贞。
懋夫人: 你不用抵赖!告诉你姐姐去,叫她自己吵上门来!我不怕的!我等着她呢!
陈彬如: 我没什么姐姐啊。
懋夫人: 谁知道你们是姐弟、是夫妻、是相好!你去告诉她,我请了律师,要告她呢!我再这儿专等着她吵上门来呢!
赵祖懋: 陈先生,你找谁?
陈彬如: 这儿是赵家吗?我找你们家的一位客人……
赵祖懋: 哦!我知道了!找李君玉?
陈彬如: 是啊,我找李君玉,她在这儿吗?
赵祖懋: (高声)君玉!君玉!
懋夫人: (冷笑)玩儿什么把戏!
幽默之外,印象最深的是(用徐念一的话说)作者对 “青年一代宽容而非赞许的同情,以及善良又不失讽刺的怜悯”(这句话总结地太好了)。[2]比如李君玉的克制和容忍,以及作为一介普通人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命运,读来确实如杨教授所说:“没有高超的理想,只有平凡的现实”。[3]以下一段是李君玉洞悉赵景荪对她的别有用心但不予揭穿,却同时有口难说心里事的那一段矛盾对抗:[4]
李君玉: 什么话,请干脆说。
赵景荪: 君玉,我干脆说,你可不要赖。我知道你的心——你是一个又谦虚、又骄傲的女孩子——君玉,你承认吧?
李君玉: 请干干脆脆的直说。
赵景荪: 我已经干脆直说了。你承认吧?
李君玉: 我又谦虚,又骄傲,好,这又怎么呢?
赵景荪: 所以你又不得已的苦衷。你觉得——当然你没什么配不上我的,不过你觉得自己的家境不如我,你不愿意高攀——我是替你说,我绝没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外公认你做了孙女儿,咱们不就门当户对了,不是吗?
李君玉: 是吗?
赵景荪: 君玉,你不该牺牲自己,现在更不必牺牲自己了。你再三叫我别招令娴生气,可是你不想想,我怎么能叫你伤心,叫你痛苦呢?
李君玉: 我?我伤心痛苦?因为不敢高攀你。(大笑)
赵景荪:(瞪视李君玉)君玉!
李君玉: (忍笑)我的天哪,简直太滑稽了!你以为我爱上了你吗?(大笑)
赵景荪: (怒)君玉!你以为我爱上了你吗?
李君玉: (笑)对不起,景荪哥,你实在太、太——你对自己——太多情了!
赵景荪: (怒)多情?你以为我爱上了你吗?我不过是可怜你!
李君玉: (笑)谢谢你,我很不用你可怜,把自己布施给我。快找令娴姐去,你再对我行好,人家就认真生气了。
赵景荪: 不用你担忧,她最知道我的心,她从不耍人玩儿。
李健吾曾表示,继丁西林以来,杨绛是中国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5]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或许更容易体会夏志清将杨钱二位齐名(而非将杨教授至于所谓 “钱夫人” 之境域)的用心。我专业不在文学批评,无法更深度地剖析杨教授的贡献,这篇文章涉及评价的部分,也大多引用前人之语。但正如这篇文章在初始提及的一点,现代社会如何纪念女性,是杨绛教授去世之际我们皆应该思考的问题。正如西方社会正逐渐尝试对历史女性重新追忆一般——如 Emilie du Chatelet(Volataire 的妻子)、Elizabeth Hardwick(Robert Lowell 的妻子)等等[6]——我们是否可以跳出仅仅对这些女性品格上的憧憬(尤其是当这些品格无可奈何地根植于一种妻子、母亲的形象),追问女性作为独立之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印记?诚然,杨绛教授这一生所经历的坎坷与其展现出的超然值得我们后辈铭记,但是然后呢——杨绛教授难不成要沦落为鸡汤一类的情感依凭?我深觉此处的 “然后” 一问甚至是比 “杨绛在她们仨中间是怎样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 张泉(译)(2006)。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Gunn, E. M., 1980.)
- 徐念一(2007)。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三座丰碑——评丁西林、王文显和杨绛的幽默喜剧(硕士论文,苏州大学,2007)。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杨绛(1993)。杨绛作品集(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此文的两段摘录受启发于 黄树红、翟大炳(2001)。杨绛世态人情喜剧与意义的重新发现——谈《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的文学史价值。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摘录来自《称心如意》原本。
- 同2
- Zinsser, P. J. (2007). Emilie Du Chatelet: Daring genius of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Penguin; Als, H. (1998) A singular woman. The New Yorker,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98/07/13/a-singular-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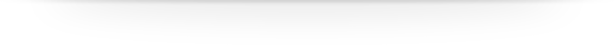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