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摊贩:半个多世纪的爱恨情仇
政府与摊贩:半个多世纪的爱恨情仇

清晨的菜市场。摊贩们将三轮车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道路两旁,有生意的忙得满头大汗,没生意的懒洋洋晒着太阳。顾客们提着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悠闲地来来往往,流浪猫在人腿间穿梭觅食,人声嘈杂,杀鱼的腥味和油饼的香气混杂在一起……
忽然,一声“城管来了”的尖叫响起,慌乱的情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蔓延开来,瞬间菜叶纷飞,鸡跳蛋打。摊贩们手忙脚乱往三轮车上搬运货品,顾客们事不关己地指指点点嘻嘻哈哈看热闹。不一会,写着城管的蓝白色小车齐整地停在路口,跳下几个身着蓝色制服的人,干净整洁的衣服与菜市场显得格格不入。有的蓝制服拿着喇叭朝着远处大声喊,有的开始与摊贩争抢三轮车……菜市场的热闹迅速褪去,只剩下污水和烂菜叶的萧索。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这样的场景都并不罕见。除此之外,一则则城管与摊贩冲突的新闻也似乎固化我们对城管和商贩矛盾激烈无法调和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符合实际情况吗?政府自始至终都是禁止街头摊贩的吗?
薛德升 和 黄耿志 两位学者以广州为例,探讨了1949年以来政府对摊贩管理的变化。研究结果证明,政府和摊贩并非一直不共戴天,而更像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1949—1977: 从“小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的重心是清除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那时候,街头摊贩的身份极其复杂:首先,他们是少资本少收入的个体商人;其次,他们是喜爱投机且唯利是图的小资产阶级;另外,一部分摊贩还扮演着间谍、地主、流氓或走私贩的角色。因此,国家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策略。
起初,广州市政府制定的过渡政策是清理反革命摊贩,同时允许那些贫困的、没有其他生计方式的商贩继续以摆摊为生。
随后,为响应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市政府决定逐步改变摊贩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形式。大多数摊贩被安排进入合作小组和合作商店工作,一些摊贩进入了国有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还有一部分摊贩被送到农村务农。这样一来,原本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摊贩就被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街头贩卖活动也基本在城区绝迹。
1978—1989:没有营业执照,也是合法商贩
改革开放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不过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规定,合法经营必须以取得营业执照为前提。
在广州,街头贩卖活动迅速复苏。但摊贩的流动性使他们难以获发营业执照,也就难以取得合法身份 。
为支持地摊经济发展,广州市政府中止执行有关营业执照的规定,容许摊贩遍布大街小巷。政府一方面想借地摊行业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带来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街头摊贩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务。
1990—2010:给我面子,就让你生存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鼓励发展市场经济。地方政府各显神通,推行各式各样的发展策略,旨在提升城市竞争力,吸引外来资本。
广州也积极地加入城市间的竞争。市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等,都让街头摊贩成为众矢之的。街头摊贩一度被当成“脏乱差”的代名词,有损广州的城市形象,降低了广州的竞争力。
于是,市政府开始重新执行营业执照的规定,为取缔摊贩提供法律依据。然而,两位学者指出,政府对摊贩的管理并没有依法依规进行。比如,取缔行动只集中在广州的“脸面”区域:一位摊主开玩笑说,政府根本不在意他摆摊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在城市的世界之外了。又如,所谓的突击行动通常只发生在摊贩的聚集地。再如,1991至2010年间,强有力的执法仅限于那些有大型活动(如:亚运会)举办的年份,因为大型活动与广州的城市形象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州市政府分区分时间的执法默许了街头摊贩在特定空间(如:城郊)和特定时间(如:夜市)继续存在。
2010至今 :疏堵结合,和谐共存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把建设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以消除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
显然,取缔街头摊贩与和谐社会的构想是相悖的。一来,城管与摊贩的冲突是社会不和谐因素;二来,夺走摊贩的“饭碗”违背社会公正。一些官员和民众便站出来为街头摊贩发声,他们认为和谐社会应该帮助和包容这一城市弱势群体。
2010年末,“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在广州应运而生。此模式允许商贩在指定地点摆摊,给予他们合法身份,同时严格禁止他们进入城市的主要干道和重要区域行商。一位城管评论,广州有三十万摊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其他谋生方式;“疏堵结合”既能保住他们的“饭碗”,又能保护城市形象。
这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政府并没有打算将街头摊贩“赶尽杀绝”。从广州的情况来看,政府与摊贩的“爱恨情仇”总是随着国内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和城市的发展需求变化,呈现出很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参考文献
- Xue, D., & Huang, G. (2015). Informality and the state’s ambivalence in the regulation of street vending in transforming Guangzhou, China. Geoforum, 62, 156-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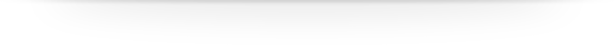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