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姑娘,圣女,还是“神奇女侠”?
灰姑娘,圣女,还是“神奇女侠”?

“身着昂贵的衣服和珠宝是有意为之,因为那显示了阿根廷穷人在贝隆将军领导下能够和我一样拥有那些东西。”——艾薇塔·杜阿尔特·德·贝隆
布宜诺斯艾利斯意为“好天气”,却也有阴沉脸的时候,空气中的水分子凝结成的薄雾潮湿阴冷。不过,雾天参观墓地却非常恰当。即便氛围诡异,还是不少人聚集在市中心贵族墓地杜阿尔特家族墓穴门口,带着猎奇的心态观看与这个家族关系并不算太大的一位女性逝者的墓牌。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贝隆夫人”艾薇塔。
随着1976年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发布,以及随后全球热卖的音乐剧,艾薇塔早已成为流行符号,甚至和切·格瓦拉一样成为阿根廷旅游纪念品上常见的头像。在真实世界里,贝隆夫人和阿根廷人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呢?

“灰姑娘坐上了南瓜车”
艾薇塔死后的遭遇颇有悲剧色彩:原本“列宁待遇”的尸首神秘消失,十几年后在意大利一个陌生名字的墓碑下重建天日;随后尸首送还给身在西班牙的丈夫,最终却没有合葬,而是分居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两地,遥遥相望。
1919年出生的艾薇塔是私生女。上层地主家庭的父亲抛弃原配,与艾薇塔的妈妈、一个马车夫的女儿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百公里外的小镇。没几年,父亲撒手人寰,艾薇塔15岁就独身一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打拼,在不少剧院和电影公司做演员打零工。
艾薇塔在大城市的第九个年头,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政府。由于军政府插手宣传事业,当时在广播业逐渐展露头角的艾薇塔认识了不少来自军政府的官员,其中有一位胡安·贝隆。
1945年,在军政府中地位越来越巩固的贝隆意外被推翻,身为副总统、劳工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贝隆惨遭流放。没几天后,成千上万被贝隆称为“无上装者”的底层工人聚集在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巨大的压力令政变者屈服,贝隆得以重新出山。随后,贝隆和艾薇塔结合,来自小镇的“灰姑娘”成了“第一夫人”。
关于那段故事情节,免不了有些争议。有人说,贝隆的两个政治盟友在政变后政府组阁的僵局中成功操纵政治,让贝隆出山;也有人(包括艾薇塔自己)表示,是她动员了那些“无上装者”,导演了五月广场那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第二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当时,工商业得到初步发展的阿根廷面临新的社会矛盾。传统农场主组成的富裕阶级占据了阿根廷大量的财富;而偏远地区的穷人大量云集到首都成为产业工人。这些穷人渴望财富重新分配,渴望成功。这时,艾薇塔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同样来自底层,体会过同样的疾苦。对了,她还是那样美艳动人、充满魅力。

艾薇塔是贝隆的“一条大腿”
当上“第一夫人”后,艾薇塔做了很多事情,成为阿根廷耀眼的明星,乃至于后世的记录者说:“在那段婚姻里,她才是那个男人,他才是那个女人。”
艾薇塔成为工会的实际领导者。她一方面推动政府制定劳工政策,另一方面通过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劳工组织监督政府。或许艾薇塔很难吸引自己生父所属的上层社会注意,但工人们却对她倾注热情。她走访车间嘘寒问暖,每周定时接待工人诉苦,广施钱粮。这种方式甚至成了贝隆政府与底层民众沟通的主要方式。
事实上,被传统农场主阶层视作敌人的贝隆政府有两个支柱,一为军方、二为工人。换句话说,艾薇塔就是贝隆的“一条大腿”。
当然,成为“大腿”也意味着不得不走“脏路”。她成功排挤了工会原来的领导人,在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信任的新人。例如,曾经贝隆曾居住公寓的看门人,虽然算不上工人,却成为工会秘书长。 </br>

艾薇塔从阿根廷“阔太太们”和教会手中接管了慈善事业。她主持兴建养老院孤儿院、建设医院、赈济灾区。虽然反对派指责新建医院做不了手术、儿童村缺乏设施,但穷人们还是把艾薇塔视作保护人,在她刚去世时,甚至把她视作圣人,在内陆还有人修建神庙纪念她。
你还可以说,艾薇塔是个“女性主义者”,在病榻上投出阿根廷女性第一张选票。她的确引导了女性获得投票权的运动,成为妇女党派的主席。她一方面呼吁女性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又呼吁她们坚守家庭角色。女性政治参与当然是社会的进步,这也意味着贝隆在1951年选举中几乎获得了全部200多万张女性选票。
对于贝隆来说,艾薇塔不仅仅是妻子,更是政治盟友,是民粹政府与底层民众交流最有效的管道。当然,艾薇塔也因此成为贝隆最大的心病。
爱“第一夫人”,还是爱“第一家庭”
“好天气城”植物园和动物园交接的那个街区,一栋古典建筑在2002年成为艾薇塔博物馆。在这里循环播放的影像资料中,艾薇塔遗体回归阿根廷、接受大量民众吊唁怀念的场景令人动容。
艾薇塔死后,贝隆做了一件事情:把艾薇塔身上的那些头衔安到自己头上。这看起来无可厚非,却成了贝隆几年后被推翻的导火索。学者分析,贝隆最担心的是狂热支持者爱的是艾薇塔,而不是贝隆政权,因此他不信任追随艾薇塔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那个曾经给自己公寓看门、深深爱慕艾薇塔的工会秘书长。

跳出当时的狂热,也不管艾薇塔那些真假不明、褒贬不一的生平。她一定是一个拥有克里斯马的政治人物。政治学视野下的艾薇塔拥有两种不同的支持者。一类是为艾薇塔个人魅力折服,从而去仰慕她的超人品格、把她视为领导者的人;而另一类真实那些会把对她的爱慕附加到一个政权或一种运动上的人。
在第一种支持者眼中,贝隆永远达不到艾薇塔的地位。不少贝隆主义者因艾薇塔的个人魅力而来,对贝隆的支持也因为艾薇塔之死而渐渐消退。1954年,贝隆下令暂停修建艾薇塔的陵墓,即是为了打破对艾薇塔的政治狂热,因为这种狂热已经对贝隆政权支持率开始起负作用。
在第二种支持者眼中,对艾薇塔的热情可以延伸到贝隆身上。在贝隆流放后,不少人坚持在1957年、1960年和1963年选举中投空白票以示对贝隆主义的支持,这就显示了一部分艾薇塔的支持者继续坚守对曾经“第一家庭”的忠诚。
马克斯·韦伯曾经在论著中表示,政治人物的克里斯马很难传递给身边的其他人,或是继承者。艾薇塔活着时,曾经做过类似的努力,她在不少地方都宣扬自己对贝隆的服从和依恋,甚至把贝隆和耶稣相提并论。从结果来看,贝隆的魅力远没有自己妻子来得那么强烈、那么势不可挡。
现实点吧,“神奇女侠”
</br>
</br>
艾薇塔的一生充满了戏剧化的情节,而在学者眼中,戏剧化恰恰正是推动形成大众文化和民粹主义的重要源泉。凭借这种特点,艾薇塔那本自传《我的使命》还频频被引用;阿根廷粉红色的总统府阳台上似乎一直有她的影子在勾留;每次阿根廷足球队输球时也总有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球场上空悲怆地回荡。
然而,对那些美好的故事的憧憬,对史诗般的形象的迷恋,就像一针的充满青春和激情的精神海洛因,不过是人类一种朴素单纯又偏执的情感罢了。而那个美好的“贝隆时代”,或者干脆说是“艾薇塔时代”,给阿根廷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br>

1952年,艾薇塔还没有去世,距离贝隆政权倒台还有几年时间。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一份学术刊物就预言,在经济重回繁荣轨道前,阿根廷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境遇将不那么令人愉快。
贝隆上台的背景是阿根廷从农业到工商业发展转型的时刻,通货膨胀一直在增长,大量底层民众期待的是获得食物和提高工资。作为一个军人,贝隆除了艾薇塔代表的底层民众这一条“大腿”外,还有军方至关重要的支持。为了巩固军方的支持,贝隆只能不断给予军方和警察力量前所未有的优厚待遇。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新官员鼓动贝隆用继续拉高通货膨胀的方法获得财富维持统治。
事实上,贝隆身边不是没有懂经济的人。一位资深经济顾问当时极力反对向英国购买铁路,但这位顾问对艾薇塔持有敌对态度,不得已被迫辞职。之后,仅有相当于60亿比索外汇储备的阿根廷花了25亿比索做成了这笔铁路买卖。
当年的分析人士不客气地说,艾薇塔介入政务,很可能给了丈夫不少专业人士不会做出的建议。通货膨胀让贝隆政府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没有取得太大成效,再加上干旱,处在富饶农业区的布宜诺斯艾丽斯居然出现了食品短缺。
这似乎不是我们印象中美好的艾薇塔,不是那么当年阿根廷人心中天降的“神奇女侠”。回归现实主义后发现,原来拉美哪有那么多魔幻。
参考文献
- Grandis R.(1999), The masses do not think, they feel,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4 (48), Special Edition: Eva Perón, 125-132.
- Young, R.(1999), Textualizing Evita: Oh, what a circus! Oh, what a show!,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4 (48), Special Edition: Eva Perón, 215-232.
- Zabaleta, M.(1999), Eva Peron and Diana Spencer: Victims of accomplices of cultural uniformity?,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24 (48), Special Edition: Eva Perón, 259-276.
- Ciria, A.(1983), Review: Flesh and Fantasy: The many faces of Evita (and Juan Per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8 (2), 150-165.
- Navarro, M.(1980), Evita and the crisis of 17 October 1945: A case study of peronist and anti-peronist mytholog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2(1), 127-138.
- Deiner, J.(1973/1974), Eva Perón and the root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Civilisations, 23/24 (3/4), 195-212.
- D. H.(1952), The Argentine façade: The doctrine of ‘Peronismo’ and economic reality, The World Today, 8 (1), 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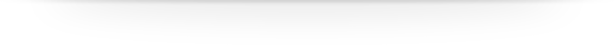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