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的力量从何而来?
劳工的力量从何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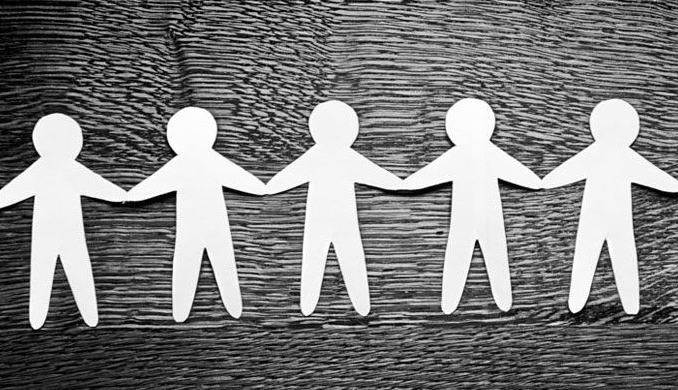
各国劳工力量的消长,由哪些因素决定?有些国家,社会政策更利于中下阶层,有效保护劳工;有些国家,劳工组织却无法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大趋势;甚至在同一国内部,不同类别劳动者的抗争能力同样高下不同。在新书《When Solidarity Works》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Cheol-Sung Lee通过对韩国,台湾,巴西和阿根廷的比较历史分析,结合深度田野和定量资料,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
书中选用的四个案例都在中等到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均在1980年代实现民主化,又都在90年代经历了艰难的民主巩固和严重的经济危机。韩国、台湾地区在文化历史上相似,曾被日本殖民、受美国影响;巴西、阿根廷均有天主教传统,经济不平等程度高,受民粹政治和国际资本影响显著。
然而,宏观结构上的相似,却解释不了他们在福利制度和劳工运动上的差异。在90年代阿根廷激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劳工组织羸弱、无所作为;但巴西的劳动力量却一直保持活跃,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未受经济危机的波及。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实行全民医保、残疾人和老人保险等福利制度,但相比而言,台湾的福利制度更多惠及中上层;原本历史条件、劳工力量和政策平等主义更好的韩国,却在新世纪经历了严重的劳动权益倒退。
《When Solidarity Works》认为,工会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职业协会等正式组织,教堂,俱乐部等非正式组织)的联系、工会与左右翼政党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劳工运动是否可以有效推动自己的政策议程,从而使国家的福利政策做出有利于劳工的调整。而工会、公民社会、政党三方关系,又植根于各国威权和民主转型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
韩国劳工运动起步:威权时代的韩国劳工组织
哪怕放在全球范围看,韩国劳工运动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
1970年,年轻纺织工人全泰一在首尔街头手举《劳动法》自焚。尚在朴正熙治下的韩国社会,首次意识到劳工问题这个“伤口”。被惊醒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主动接触最底层工人积极分子,通过城市工会和工人夜校暗中结识新人,建立起最初的劳工—公民社会网络。
1980年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新的民主化局面逐步开启,学生与劳工间的地下合作也达到顶峰。连续好几年,几千名大学生相继主动退学,他们和那些因参与示威而被开除的学生一道,隐瞒身份进入工厂工作。尽管工厂管理体制封闭,这些学生依然尝试开办左翼读书会,组织工人静坐、示威、罢工,还帮助工厂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沟通网络。
暂时留在校园的大学生则继续推进左翼思潮。当时,高校新生或多或少都在大一、大二接触左翼学生团体。到80年代末,韩国校园的左翼组织已成为一个多层极,跨校园的组织,涌现出不少积极人士。
这些学生的早期活动和人生选择,奠定了韩国劳工运动的组织基石。民主化开启后,多数人继续投身公民社会,要么继续留在工会任职,要么开办新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职业选择天然拉起一张韩国民间社会组织大网。因此在韩国,工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从最初就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在此之上,1995年著名的“韩国民主劳总”(KCTU ,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成立,代表三分之一的劳动者,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协调和动员核心。KCTU和公民社会的广泛联系,最终推动了改革派政府的政策议程。除此之外,1994年成立的民主人民联盟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PSPD)作为介于社运组织和政党之间的机构,既是KCTU的伙伴,也在转型时期成为连接工会和政党的另一大平台。
威权时期建立的劳工—公民社会网络,在转型期推动了多次大罢工,几乎导致经济瘫痪。特别是1997年前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总统换届和劳动法争议三重困境,公民组织之间的联系达到了顶峰。Lee根据组织间的成员共享和社运参与而绘制的网络图显示,几乎所有大小组织都嵌入到一张大网中。牢固的联盟关系推动了2000年民主劳动党的成立。许多工会主席加入新政党,很多民间组织赞助劳动党竞选。
韩国劳工运动衰落:发生了什么?
然而2000年之后,韩国劳工运动的形势不仅没有巩固,反而急转直下。被公众寄予厚望的卢武铉上台后,却开始推行不利于劳工的政策。原有的良好运动根基是如何慢慢丢失的?究其原因,Lee认为,社会组织内部分歧、工会与公民社会关系恶化,以及社会组织的制度化造成了不利于劳动组织的政治机会结构。
首先,早在金大中时代,KCTU内部就在与政府互动策略上有巨大分歧。制造业工会反对任何妥协;白领则仅希望减少损失。各方对是否参与官方支持的劳资、政府三方委员会无法达成共识,导致第一届KCTU委员会总辞。随后,两届KCTU领导人均为激进女性劳工社运家,对金政权和后续卢政权充满怀疑,拒绝参与三方委员会。这两期领导者甚至认为,和公民社会的部分合作弊大于利。特别是2003年卢武铉压制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会罢工,激化了工会对政府的不信任。
其次,随着时间推移,KCTU本来的伙伴PSPD开始构建独立组织体制,绕过工会介入政策和政党事务。PSPD的政策动员力慢慢领先于KCTU,在同时期提出议案数量是KCTU的近三倍。然而,KCTU却认为PSPD的动员框架只会让当政的温和民主党得力,不会真正照顾到劳工,两者的合作关系也转变成竞争关系。
第三,卢武铉和李明博执政期间,民主党积极收买左翼社会组织,很多组织领导者进入体制内政党,和劳工组织的关系疏远。比如PSPD两位创立者,一个在2011年成为首尔市长,另一个于2012年晋身民主党议员。
最后,民主劳动党的成立让工会有更直接的政策表达渠道,但渠道便利让劳工组织忽视继续和执政党合作的重要性;劳工组织与民主劳动党接触更频繁,也让执政党有理由疏远劳工议题。2005年后,KCTU和主流政党的关系几乎完全斩断。清醒过来的领导层试图重回三方委员会,却发现当政者已经和另外亲政府的工会联盟合作,KCTU彻底被体制拒绝在了谈判桌外。
博弈:与公民社会组织联系成为胜负手
新世纪后韩国的劳工力量总体倒退,却不妨碍在部分政策领域取得进展。2007年、2012年韩国保守党新国家党在选举中连续获胜,并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势不可挡。但劳工与公民社会的团结还是能够解释在部分领域取得的进展。
在医疗保险领域,不少专业组织,如全国医保联合会(NCHIU),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反而比同一时期的KCTU更加紧密。由医疗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Solidarity for Health Rights (SHR),成功抵制了医疗市场化改革。他们的抗争策略也极为多元:在全国放映迈克尔·摩尔的《医疗内幕》、组织大规模烛光示威、开新闻发布会反对济州岛建立盈利性医院、积极利用互联网推动反私有化运动、推荐专家在主流媒体解释医疗盈利化的危害、在报纸上刊登相关广告,甚至专门派人到济州岛,挨家挨户宣传盈利性医院的害处。
就这样,在劳工运动总体环境最差的时期,医疗领域的政策不仅没有显著倒退,还在大病医保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
同一时期,养老金领域情况却截然相反。事实上,1990年代劳工运动参与者因为年轻,没有特别关注这一领域。当时,养老金受益者主要是等级意识和服从习惯较强的退伍军人和军官,没有出现相关利益集团。因此,主要工会组织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NPS) 没能和其他公民组织建立强大纽带,也没有积极招募相关政策专家。
更关键的是,主要工会联盟同样忽视草根联盟的重要性。保守党上台后,不管是激进的KCTU还是相对保守的FKTU,都没有对削减养老金做出实质性抗议,只留NPS孤独抗争。左翼政策专家的缺席,也使该政策领域完全被亲政府专家和官僚垄断;主流媒体不断给民众灌输国库将空的预言,民间组织则拿不出任何反驳意见。
由此可见,即便同地同时,工会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一样决定了劳工组织努力的效果。
“遥远的相似性”:台湾与阿根廷的劳工政治
尽管韩国与台湾的文化背景有相似性,但台湾地区的劳工动员结构却与南美的阿根廷更为接近。
韩国劳工运动发源时期,并没有与政党结盟;与此相比,台湾地区的劳工运动却与威权时代的“党外运动”齐头并进。戒严时代,“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CFL”不能代表工人权益,民进党试图自行打造工会。由于国民党压制基层组织,威权时期的工会没有独立生存的政治空间,不得不依附于党外势力表达观点。
这种劳工运动依附于政党的关系延续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民进党孵化的“台湾工会联合会(TCTU)”成为合法组织,却活在民进党“阴影”中,无法独立动员劳工;民进党无时无刻不在收买TCTU,邀请后者成员作“立法委员”。2004年,大部分TCTU成员已被民进党吸纳,TCTU彻底变成只开例会不做动员的官僚机构,与CFL走上同样的建制化命运。
相反,由知识精英主导的组织“台湾劳工阵线(TFL)”在政策上有更多的斡旋余地。TLF扮演智库角色,在政府、劳工之间斡旋,帮劳动者解决法律问题。但是由于TFL本身在社运上的疏离态度,无法和韩国的KCTU比肩,外界也一直批评其立场没有脱离民进党影响。
台湾地区社会福利领域的各种政策成果,与其说是劳工运动的产物,不如说是得益于蓝绿两党的政治博弈。这种博弈是否对工人有利,并不受劳工运动控制。
阿根廷劳工运动的困境与台湾类似,即劳工运动与执政党间的历史联系阻碍了发展。从贝隆1945年组建正义党前身工党,到1983年民主转型开始,阿根廷劳工组织受到贝隆主义的极大影响。军政府统治期间,工会及其非正式的足球俱乐部被用于秘密会议场所。很多进步人士因没有正式表达渠道,也常借工会发声。
由于曾经受益于贝隆的正义党,阿根廷的劳工组织对似乎倾向于左翼的执政党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于代表正义党的卡洛斯·梅内姆1989年上台、大刀阔斧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劳工力量完全没能集聚起反抗力量。梅内姆上台三年后,主要工会组织全国劳工总工会(CGT)才组织了影响有限的罢工,而且还还不被旗下的挺政府分支所支持。CGT软弱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工会与政府存在太强的历史联盟,却没有在更广泛的公民社会中扎根。所以当政府往左,工会暂时受益;政府往右,工会也没有挽救办法。
面对CGT的软弱,一部分人愤而离开,于1997年建立了更有代表性的“阿根廷劳工联合会(CTA)”。CTA动员公民社会力量,于上世纪末组织多次示威。更重要的是,他们团结人权、移民、女权组织及学者智库,鼓励成员参与和邀请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加入,提升了公民社会和劳工的凝聚力。最终,公民社会在推动基什内尔左翼政府上台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使得阿根廷的劳工运动形势逐步转好。
巴西:劳工力量从未衰退
韩国、台湾、阿根廷、巴西这四个研究案例中,巴西的劳工环境和运动策略一直都是最好的。定量网络数据显示,以组织成员共享为标准,巴西的工会组织确实于政党、其他专业组织及非正式组织紧密联系,组织密度比其他三地高出许多。同样在90年代经历经济危机、同样受全球化和外资极大影响,巴西的劳工力量从未衰退。
事实上,巴西劳工组织的发展历史和韩国最为接近。威权时期,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社区进步教会、学校的地下合作非常多。工会活动往往在草根社区发起,受当地社区积极支持;社区维权组织也得到工会鼎力相助。工会与社区协作共生的模式曾被学者Seidman(1994)详细论述。这种背景让工会在民主转型时期代表性更强。
作为70年代起巴西独立劳工运动的最典型代表,巴西劳工总会(CUT)早期局限在为传统的制造业工人争取权益,之后年轻领导者把服务群体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并寻求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相比之下,阿根廷CGT工会视野就比较狭窄,只为狭义的工人群体服务。巴西工会议程包容性高,不少女性领导者不仅提倡劳工权益,也有空间去倡导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权利。通过把劳工权益视为一种普遍人权,他们也凭借更多身份进行政治动员。
除去在街头的影响力,CUT本身的政策动员力也很强,他们的政策专家积极参与巴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研究所 (DIEESE) 的工作。DIEESE由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领域学者组成,在政府制定的劳工政策,如最低工资上,有很大话语权。
另外,巴西成熟的左翼政治还源于立足草根、发育于社区运动的政党政治。80年代末发轫于愉港的“参与式预算”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很多巴西城市,治理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抗争政治和政党政治有着相似的源头。
未来的斗争策略
当然,本书并不能解释全部的劳工政治差异。Lee并未阐述公民社会和政党的关系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到劳工运动。他过分突出了劳工运动本身的自发性,对政党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自发性如何影响劳工运动的动员结构则未多着墨。Lee也未能详细论述非正式组织,比如各种教会和俱乐部如何在三方关系中起到作用。
然而,以一本著作的篇幅来看,Lee的分析已涵盖多个社会运动、福利国家和劳工研究中的问题。全书自成一体,而且在各个层面呼应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成熟民主国家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
首先,这本书强调了历史因素对动员结构的影响。威权时期,学者、工人、教会联盟可以为后来的劳工组织打下坚实基础。这种历史视角在其他社会组织著作中并不少见,如比较典型的LeBas (2011) 对非洲反对党的研究。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威权政府建立了国家主导、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来控制基层,却制造了自己的“敌人”:正是这些工会后来成为培育反对党骨干的温床;相比之下,肯尼亚并没有统一工会,也就没有生长出强大的反对力量。
其次,书中分析了政权在回应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同时,也会精心吸纳和收买反对势力。这在韩国和台湾的案例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去年,学者 Eidlin (2016) 对美国缺乏工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做出了相似阐发,正是民主党成功地在大萧条期间吸纳了工人反对派,美国才没有出现更激进的左翼政党。另外,工会和社会组织也需反思如何最大化地利用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而不是让身份政治瓦解了统一的抗争议程,前文的巴西CUT就是成功联合社会各阶层的例子。
社会组织制度化为政党后,不能仅通过左翼政党来发声,也要继续和执政者保持联系,否则运动成果往往不可持续。特别是新政党上台后,旧有政策很可能倒退。Amenta (2010) 等学者曾经在相关综述文章中发现,成功的社会运动可能不能持续,失败的运动却能留下很多遗产。McVeigh (2014) 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3K党当年的活动尽管很快消退,却对美国南部的政党重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K党活跃的区域,投票转向共和党的人多了5%,并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
另外,传统社运研究往往重视运动如何兴起,却忽视运动如何消亡。Davenport (2014) 对美国新非洲共和国(1968年成立于底特律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是个例外。他发现社运衰落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高压下,组织成员对国家压制的不确定感,及内部信任的瓦解。而在Lee这本书中,KCTU内部在如何抵制国家政策、如何与其他组织结盟上分裂,导致了其后期衰败。
最后,Lee也为左翼指出了不同时期的斗争策略:在政治机会结构有利时,应注意提升与现有政党的联系;在机会结构不利时,则需与公民社会创造强有力纽带,用广泛社运联盟发挥作用。
政党轮替是暂时的,动员结构的积累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下不满川普的人们,应该可以从书中巴西和韩国的例子中找到突破动员瓶颈的思路,也应该能从阿根廷和台湾地区的例子中找到失败的教训。抗议的规模并不能自证成功,人们今日的努力,可能要等多年后才能换来成果。
参考文献
- Lee, C. S. (2016). When solidarity works: Labor-civic networks and welfare states in the market reform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enta, E., Caren, N., Chiarello, E., & Su, Y. (2010).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287-307.
- Davenport, C.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idlin, B. (2016). Why is there no labor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rticulation and the Canadian comparison, 1932 to 194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 (3), 488-516.
- LeBas, A. (2011). From protest to parties: Party-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Veigh, R., Cunningham, D., & Farrell, J. (2014).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outcome 1960s Klan Activism and its enduring impact on political realignment in southern counties, 1960 to 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6), 1144–71.
- Seidman, G. W.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核心书籍:
其他文献: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