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听我的命令:撤!
兄弟们,听我的命令:撤!

在某个不存在的搜索引擎上检索 “撤退” 或 “撤兵”,分别得到 645 万个和 239 万个结果;检索 “开战” 或 “开火”,分别得到 298 万个结果和 112 万个结果。看起来,“撤” 这件事似乎还蛮受欢迎。
一
最近看了《敦刻尔克》,汤姆·哈迪背对夕阳,点燃飞机,从容地等待德军过来俘虏自己,就好像一场辉煌的胜利;渡尽劫波的残兵坐着火车回到英国,民众追着火车送啤酒,像是迎接回家的英雄。这样的撤退,并没有让英国在战争中一蹶不振,反而激发了极大的热忱和勇气。
在真实的历史中,1940 年 6 月 4 日,撤退任务结束,老炮丘吉尔也不得不在议会中提醒大家冷静:“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 尽管丘吉尔呼吁清醒,但他没有忘记用撤退激发 “作战到底” 的情怀。这个英语世界优秀的演讲者用一连串的排比句说出那句 “决不投降”,鼓舞了刚刚在欧洲大陆被打蔫了的远征军,也鼓舞了同盟国把英国作为欧洲抗德基地。
归根结底,撤退是精确的政治计算,每一个动作都有成本和收益。在政客的眼里,撤退不仅仅意味着士兵的生命,还意味着宏大的政治格局和微妙的个人进退。
2000 多年前,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在温泉关失守后撤得连家都不要了。面对薛西斯的不死军,伯罗奔尼撒人恨不得把希腊所有军事力量都龟缩到柯林斯地峡。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这次再也不退,连哄带骗地拉着希腊联军和波斯人在萨拉米斯湾海面决战。地米斯托克利撤,保住了雅典人的命;不撤,把自己的政治声望推到顶峰。不管是运气好,还是诡计多端,地米斯托克利把撤不撤玩得极其通顺。
二
任何社会中,战争都需足够的合法性。即便政客们追求的是某种十分重要的利益,而且不需要国内全面动员,只要缺乏这种利益不致命,也很难说服老百姓持续支持战争。好死不死,对手也了解这一点,当然会死缠烂打消磨战争,等待你国内反战声浪滔天。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国遇到难啃的敌人最容易失败,因为大国总是没法坚持到最后。这就是美国失掉越南的原因之一。
就算战端初始时得到拥护,但随战事延续,支持始终是一条向下的曲线。战争延续时间越长,支持率越低,战力就越差。不少学者认为,民主制度的优势体现在民主国家发动的战争基本上都取胜了。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这种政体下输掉战争意味着有人要失去职权,所以政客只在取胜几率大的时候兴兵作战。换句话说,民主国家挑选的对手往往是力量对比明显、能够保证速胜的倒霉蛋。比如,美国进攻格林纳达、英国奔袭弗兰克群岛。
一旦开战,民意支持率、国内政治博弈始终是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谈判无果、升级成本过高,在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率降到某个尴尬的时点,决策者往往不得不下决心逐步撤军,寄希望于支持率随着撤军开始逐步回升,到达可接受的平衡点。
遗憾的是,对于政客而言,这种想法过于幼稚。基辛格在写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说过:撤军就像咸花生,只要开吃,就还想要更多,“回家的美军士兵越多,公众要求的撤军数量就会越多”。做出撤军的决定很艰难,因为没有人在心理上愿意接受一个看上去正在失败的战争。所以,自己生产出来的导弹,硬着头皮也要打出去。
用撤军换取公众支持在逻辑上同样说不通,因为撤军同时损害军事和外交能力。越南的黎德寿 1970 年在巴黎谈判时很豪气地跟美国人讲:美国当然可以让越战 “越南化”,逐步撤出美军、训练南越傀儡军,但傀儡军什么时候能中用呢?100 万美军加南越军都打不赢的仗,完全让傀儡军接手,你们能赢么?
这就涉及到关于撤军的另一想象:撤军会迫使当地盟军提高作战。可惜,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很难训练出军队,他们缺乏有经验的指挥人员、缺乏物流和空军能力。重要的是,当地政客最怕的是自己阵营中出现一个强大的军事强人。最近的栗子是,美军撤出伊拉克后,曾经到处流窜的 “伊斯兰国” 似乎就在伊拉克生了根。
三
当然,撤军也有妙处。对于美国这种国家来说,撤军并不仅仅是脱离战场或避免死伤,也是为了摆脱 “承诺陷阱”。
冷战时期,美国希望亚洲盟国全面改革,以强化控制国内局势的能力。可惜,这种努力基本都失败了。盟友不改革,不是因为认为美国老大哥不可靠,反而是认为老大哥太可靠,就算不按要求改革,老大哥一样会出钱出兵,所以犯不着费劲。在这种状况下,一旦做出了对小兄弟的某种承诺,你就失去了所有谈判筹码。
所以,美国在很多时候宣称 “不听话就撤军” 时,很可能是为增加在盟友中的谈判筹码。但吊诡的是,盟友往往有许多国内派别,有些派别巴不得干涉军早早离场,而且不同派别之间的偏好永远在变,撤军很容易变成对某些派别的 “奖励”。另外,盟友还会认为,如果满足美国的要求,还不能做得太好,因为情势太好后很可能让美国人的存在变得不必要。
小布什当政时,拒绝以从伊拉克撤军作为要挟伊各派别和解的条件。原因可能是他并不认同 “承诺陷阱” 这一逻辑,或者认为从伊拉克撤出力量风险太大。但事实上,不少伊拉克公众已认定美国人离开是当时实现和解的前提条件。
所以,在后来的博弈中,拒绝撤军的美国被伊拉克人要求离开。
四
对于政客而言,和战是一道精算题。
两军对垒,谁也不会轻启战端,因为开火容易,但撤军难,谁也难以保证所有撤退都像敦刻尔克一样边际收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经常看到两国口舌交锋,却极少直接撸袖子开干。只有想清楚成本收益,才会像普京那样直驱格鲁吉亚,迅速完成目标并干净离场。
面对邻国纠缠时,大国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打,能不能赢,拖不拖得起?
与撤军类似,避免陷入莽撞的 “承诺陷阱” 也是大国要做的一道数学题。不仅与对手交锋要计算,与盟友打交道也要计算,若即若离有时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利益,全情投入往往掉进别人家的权力游戏。
面对小兄弟肆意挥洒时,大国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控制?要不要在损益变化前离场?毕竟,你不是预言家开天眼,没谁是 “真·金水”。
所以,该撤时撤、该进时进,是为能屈能伸。
参考文献
- Jervis, Robert. “The Politics of Troop Withdrawal: Salted Peanuts, the Commitment Trap, and Buying Time.”
Diplomatic History 34.3 (1), (2010): 507-516. </br>
- Zelizer, Julian E.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Troop Withdrawal.” Diplomatic History 34.3 (2010): 529-541.
- Lawrence, Mark Atwood. “Too late or too soon? Debating the withdrawal from Vietnam in the age of Iraq.”Lawrence, Mark Atwood. “Too late or too soon? Debating the withdrawal from Vietnam in the age of Iraq.” Diplomatic History 34.3 (2010): 589-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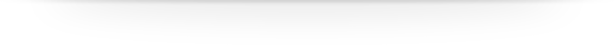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