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子宫,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吗?
出租子宫,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吗?

马盖先/特约作者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他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在印度的班加罗尔,无数工人阶级女性带着改善生活的期望,前仆后继地进入跨国代孕市场,以出租子宫的方式换取相对高昂的劳动报酬。在《Discounted Life》一书中,Sharmila Rudrappa(2015)在代孕机构——Creative Options Trust for Women(COTW)——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访谈七十位代理孕母和二十对试图成为父母的伴侣(intended parents,即寻求代孕服务以试图成为父母的同性或异性伴侣),分析了代孕这一新兴劳动在全球化潮流下的兴起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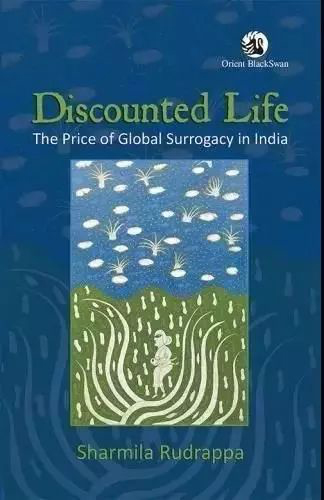
在印度,代孕这种人工辅助生殖的技术是合法的劳动,而2010年,印度的“援助再生产技术法案”(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Bill)更是鼓励第三方代孕中介机构代为招收代孕者并为其提供专业的代孕环境,透过这种外包代孕的运作模式以防止不孕不育专家在直接僱佣孕母的过程中损害孕母的劳动权益。
与许多民间代孕机构类似,COTW宣称自己是非营利的代孕组织,强调组织的“社会企业”性质,在他们看来,代孕这件事可以帮助无数家庭摆脱不孕不育的困扰,更重要的是,这对从事该劳动的工人阶级女性而言也是一种赋权,这样的赋权不仅包括缓解经济负担、还包括透过劳动获得责任和自尊。代孕,融合了新兴再生产医疗技术与需求旺盛的生育市场,被印度民间认为是一项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事业。
那么,成为代理孕母,真的可以自我赋权吗?Sharmila Rudrappa的田野调查发现,代孕是一项高度剥削劳力的工作;然而,在这些孕母的眼中,代孕却是一件给予她们力量和生命意义的事业。代理孕母一方面对“出租子宫”这一行为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经济理性,但另一方面又缠绕于这一工作给她们带来的污名与负面情绪之中。代孕劳动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于“生育和母职之间存在一种难以剥离的连结”的原始想象,将女性的身体彻底地商业化,而承担代孕劳动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女性,在本书的案例中,还是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因此本书对代理孕母的讨论涉及全球化、生育、性别、种族、阶级等多个面向,回应作者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再制这一议题的关怀。

本篇以该书的代理孕母作为书写对象,以“代孕是自我赋权还是再制压迫?”这一疑问来组织本书对代孕产业的讨论。本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将讨论“代孕如何可能?”,即“婴儿商品化”这一共识如何导致代孕的兴起,而班加罗尔的工人阶级女性又该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代理孕母呢?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将着重回答“赋权与压迫”之间的张力:为何工人阶级女性认为代孕给她们带来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赋权呢?这到底是一种真正的赋权,还是只是她们对剥削的误认?第三节紧接着讨论,如果代孕并非自我赋权,那它对工人阶级女性的压迫到底是什么?
婴儿商品化:“生育与母职”不再具有神秘连结
诸多原因使许多试图成为父母的伴侣(intended parents)无法生育小孩,比方同性伴侣、患有生理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夫妻、被领养制度限制领养权力的同性夫妻等。书中的客户大多是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产或者上层阶层伴侣,为了拥有小孩不惜重金且远渡印度寻求帮助。同时,他们也努力让自己成为合格的准家长,而这一自我塑造方式主要透过消费来完成,例如花钱进行准家长培训班、进行家装布置、为代理孕母购买礼物等。 </br>
如果说这些试图成为父母的伴侣用金钱购买婴儿和怀孕的体验,那么代理孕母则用婴儿换取金钱。进行一次代孕,这些女性可以获得4000至8000美元不等的酬劳,对于生活处于贫困线之下的工人阶级女性,这些报酬是可观甚至是优渥的。26岁的卡拉这样对作者说,“我要还贷款,我还有家里的困难,如果没有捐精和代孕这些事,我上哪里去赚这么多钱!”
不少民间人士和学者均宣称婴儿是爱的产物而非商品,在他们看来,代孕过程中,被出租的是子宫、而非婴儿本身。但是,Rudrappa则认为在代孕过程中,各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子宫无法脱离女人的身体而独立存在,因此,代孕本身是女性身体被严重异化的一项劳动。
具体来说,孕母的身体需要时刻进行超音波检查;她们也需要注射荷尔蒙以维持生育需求;必要时,她们还要注射氯化钾选择性地堕胎;不少孕母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在分娩之中进行剖腹产,一旦小孩出生便立即被抱走;并且,孕母不得与刚出生的婴儿进行任何互动,甚至连一眼都不得见。据此,基于卡尔波兰尼在经典作品《大转型》的中提出的“市场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Rudrappa认为,婴儿是为了交换而生产出来的真实的商品,而非虚构商品(p107),而代理孕母在代孕的环节中只是一个生产工具。

那么,对工人阶级女性而言,除了承担上述的医疗风险与身体伤害,她们该如何从心智上成为一名“合格”的代理孕母呢?我将其概括为避免与母胎建立心理连结。在孕母们看来,与胎儿产生心理连结是“不必要且不专业”的。比方说,上文提到的卡拉在面对作者关于“是否因为将婴儿拱手让人而感到难过”这一质疑时,她说道,“绝不!从一开始你就必须说服自己‘这不是你的baby喔!’你要时刻牢记,这是别人的小孩。我对他/她没有感情。爱小孩是一种负担,我不想和这个婴儿有任何连结,所以我不应该投入任何感情。我已经有自己的小孩了,我来这里(代孕机构)是为了帮助我的家人、处理我的生活困难的。既然如此,我干嘛还给自己带来新的负担?”
可见,在代孕过程中,孕母们积极地摆脱与胎儿的情感连结,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在家庭中的母职和义务,另一方面,把生小孩这件事摆放在市场中,将其视作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的手段。
由此,在婴儿商品化的论述下,代孕被合理化为一件正当的劳动。而孕母的代孕行为本身也不断地将女性身体进行异化。接下来,我将开始分析,代孕对工人阶级女性的“赋权和压迫”。
自我赋权如何可能?
代理孕母们为什么会认为她们在代孕过程中获得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赋权呢?本书指出,这是因为代孕带给孕母们更为良好的劳动条件,同时,孕母们也从代孕中获得对劳动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br>
首先,本书中的孕母,在进入代孕行业前,大多是成衣厂的女工。班加罗尔是印度成衣制造厂的重要聚集地,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女工均有负面的工作经验,例如超长工时(一天十二小时甚至更多)、超低工资(一个月100美元)、严苛劳动条件下累积的疾病(尿道炎、贫血、头痛)、工厂内性骚扰(在工作场所经常遭受男性管理者的骚扰)、加班加点而导致回家被怀疑红杏出墙等。总之,成为代理孕母之前,工人阶级女性的工作未被肯认,她们难以体尝劳动的价值感。
进入代孕行业之后,这些女性的报酬明显提高(一次代孕在4000至8000美元不等),这样的“高薪”可以暂时帮助家人度过经济困难。同时,她们居住在COTW的宿舍中,尽管宿舍安装监视器,但是她们在宿舍中却能够暂时摆脱繁重的工厂工作和家务,更重要的是,身为孕母的她们被人服侍和优待,她们也有机会认识其他同为孕母的朋友,这些生活经验是长期从事艰苦的工厂工作无法获得的。因此,不少孕母发现, 代孕带给她们相对优渥的物质反馈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这让她们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其次,孕母们从代孕中获得价值感。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孕母们认为,她们生产出的是“婴儿”,一个会改变、成长的生命,而非像在成衣制造厂中生产出一块布料那样单调乏味,因此,孕母们将生产婴儿看作是一件无比有价值和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价值也体现在这份工作的道德感,作者在书中用“礼物”(gift)一词来形容孕母们对代孕工作的道德评价,在孕母们看来,她们牺牲自己的身体,满足了许多家庭的求子愿望,她们的子宫帮助许多家庭圆梦。
例如,27岁的芊德拉这样描述她对代孕的看法,“我对代孕做出了很多牺牲啊,但是这样子能够给另外一个家庭带来小孩耶,这会让他们满足,他们不再失落了!”可见,尽管孕母们起初带着对经济回报的期望进入代孕市场,但是在她们心中,代孕这件事本身仍然是充满道德的且高尚的,她们也因为给其他家庭带来生命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自我价值感。
再生产工业的压迫再制
尽管代理孕母对代孕具有正面和积极的定位,但是作者指出,这一劳动形式,镶嵌在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结构下,仍然是剥削性的。这一小节将分析工人阶级女性在代孕过程受到的压迫,其中不少剥削是隐而未现,甚至被合理化的。 </br>
首先,压迫表现在隐性的经济成本。如开篇所说,代孕机构和民间社会普遍将代孕当作一种社会企业,从事该劳动的工人阶级女性得以获得优渥的经济报酬,因此,他们认为这对于试图成为父母的客户们和代理孕母们而言是一个双赢交换(win-win)。然而,Rudrappa则指出,判断是否为双赢的商业交换需要视个人情况而定(p151),这是说,金钱对不同阶级的人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26岁的西塔从事代孕之前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然而,一场意外车祸夺走了她的孩子,丈夫也重伤送医,西塔一家瞬间陷入贫穷,无奈之下,西塔以从事代孕试图偿还14000美元的债务和医疗费用。
如西塔一般,孕母无一例外顶着家庭经济负担从事代孕工作,在与作者的对谈中,孕母们在代孕过程中承担巨大的身体苦痛,同时她们肩负着改善或者支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一次代孕的四千美金酬劳看起来虽然不少,但是扣除在班加罗尔的生活保证金(2000美元)和房租(月租50美元),这笔报酬所剩无几。

作者认为,这些金钱对于客户家庭而言是奢侈性消费,但是对于工人阶级女性则是支撑家庭多活一天的救命钱,甚至,这些金钱只能用来暂时填补家务经济的漏洞,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贫穷。因此,在外界看起来收入还不错的代孕酬劳其实无法真正改善孕母们的生活处境。
其次,压迫也包括隐性的情感付出。即便孕母们时常提醒自己不能与婴儿产生情感连结,但是正因为一刀切断与胎儿的情感依附其实充满痛苦和恐惧,她们才需要在怀孕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与胎儿的“理性关系”,本书中,不少孕母在交换小孩之后产生了对小孩的思念和悔恨,而这些情绪又夹杂着对自己所属家庭的责任感,使孕母们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
此外,孕母们的情感付出还体现在与客户家庭的互动。一般而言,小孩一旦出生便被带走,客户家庭十分担心孕母与小孩维持连结,进而影响客户家庭的亲密关系的培养,芊德拉这样表达自己对客户家庭的不满,“我的牺牲给那些家庭带来新的生命,但是那些家庭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以为我和他们维持联络是为了向他们要钱!他们这样做(拒绝孕母与小孩和家庭产生连结),以后要怎么面对他们自己和小孩?”
在孕母们看来,一旦生出小孩之后,她们便被强制斩断与客户家庭的联系,因为客户和代孕机构都十分忌惮孕母们会以此进一步获得物质交换,这种不信任感无法让孕母们感受到自己的劳动被真正尊重,在她们看来,小孩出生之后,身为孕母的她们便注定被遗弃(p159)。

这种不信任感则是孕母受压迫的第三种表现,即代孕工作的污名化。作者指出,尽管民间社会将代孕渲染为一个对社会卓有贡献的行为,但是在客户、孕母、代孕机构彼此的互动之中,孕母和代孕工作都是被高度污名化的。“什么样的女人会愿意将如此神圣的生殖能力出卖出去来换钱呢?”带着这样的质疑,客户家庭和代孕机构认为,孕母们由于有迫切的经济需求而出卖小孩子,这是极其可怕的,她们可能为了金钱而做出任何事,因此,她们是没有道德的行动者(p156)。
吊诡的是,试图成为父母的客户家庭和代孕机构用以批评代理孕母背后的逻辑正是孩子是神圣且不可交换的,然而,他们寻求代孕却同时应用了婴儿商品化的逻辑,这样的双重标准展示的是代孕市场的权力不平等。进一步地说,孕母承受的污名化体现的是阶级差异,她们的行动是做出贡献抑或是缺失道德,其实掌握在主导着代孕市场的需求和运作的人们手中。
代孕行业的“再生产正义”
当孕母罗帕得知Rudrappa“写我们孕母的故事”时,罗帕说道,“所以,当我女儿长大读到妳的书时,她就会知道我当年是如何努力工作来养活她的咯!” 成千上万的代理孕母转让刚从自己腹中生育出来的小孩,以养育自己家里的小孩,这一项在自由市场大行其道的再生产劳动,在作者Rudrappa看来,充满了阶级与性别的歧视。 </br>
“再生产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是作者用以讨论代孕的理论框架,她认为,我们应该整体性地考虑女性在家庭、工作、学校或任何可能改变她们所属权力关系的位置,这种对女性经验的整体考量还考虑在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对女性工作者的影响。
Rudrappa也表示了自己对代孕工作的立场,即她期待孕母能够从工作中得到自尊、能够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能够自由选择生育和待产的方式、能够和客户家庭维持她们期望的连结(p174),她期待国家保障代孕工作者和家人的生活权益,以防止自由市场进一步剥削代孕劳动力。

Rudrappa的向往回应了基本的人文关怀,但是在代孕尚未正式合法化的中国,这样的期望似乎是“乌托邦”的愿景。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起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1]显示,我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已经高达15%,这意味着每8对育龄夫妇就有一对夫妇受不孕不育的困扰。加上2016年二胎化政策的放开,国内对生育的需求日加强烈。然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则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面对国内庞大的代孕需求,许多中介机构纷纷转至地下经营,也就是说,在代孕这个灰色交易市场中,孕母缺乏合理的劳动保障,代孕是一件极具风险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孕母的权利保障和“再生产正义”之路显得更加艰难。
关于代孕及其合法化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 | 政见 CNPolitics
《代孕:合法还是不合法,这不是个问题》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