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塔米·金:李箱的诗
E.塔米·金:李箱的诗 ——
李箱的诗
E.塔米·金/文
王立秋/译
E. Tammy Kim, “The Empire Within”, The Nation, May 3, 202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culture/yi-sang-selected-works/。原题为《内心的帝国:李箱的全球诗》。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做商业用途。
E.塔米·金,韩裔美国作家,编、著有《朋克民族志》(Punk Ethnography),经常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和《纽约客》在内的多家媒体撰稿。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在阿兰达蒂·罗伊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和大获成功之前不久,她受邀参加伦敦的一个实况广播节目。看起来事情和计划的不一样。就像她在2018年的一次讲座中回忆的那样:
另一名嘉宾是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在回答访谈者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赞美了英帝国主义。 “甚至你”,他傲慢地转向我说,“你用英文写作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在向英帝国致敬。”当时还不习惯广播节目的我沉默了一会儿,就像一个新开化的,行为得体的野人应该做的那样。但后来我有点情绪失控,说出了一些非常伤人的话。那个历史学家很是不安,在节目后他告诉我,他那么说的意思是在称赞我,因为他喜欢我的书。我问他,他是不是也觉得爵士乐、蓝调和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写作与诗歌实际上都是在向奴隶制致敬。拉美文学是不是也是在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致敬。
把罗伊的书归功于帝国显然是荒谬的。她的小说是在英国正式退出南亚次大陆五十年后才出现的。但那个历史学家的评论指向一个甚至更不成熟的判断。“英语和印度这个理念本身一样好或一样坏”,罗伊在她的讲座中指出,在她的生活中,英文也类似地桀骜不驯。她父母在短暂地在一起的时候说英语;罗伊小时候,在学会母语巴加尼语(Baganiya)后就开始学英语了。罗伊评论说,在一个有近800门语言的国家,英语变成了“在实践上解决”殖民主义创造的各种问题的“方案”,也就是说,英语变成了一种区域性的,对更加政治化的印地语的抵抗。
罗伊引用了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用它来证明,内生的语言也可以被用来压迫和伤害。反过来说,她认为,B.R.安倍卡的《消灭种姓》则表明,用帝国的语言写的文本,可以指示和拆解“特权与排除”。因此,“英语继续有罪地、非官方地、默认地存在着。”
言语与帝国、殖民臣民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也是前卫现代主义者李箱的诗、散文和小说中的一个持续的潜台词。在短暂的一生中,李箱既用他的母语韩语写作,又用他被迫接受的日语写作,同时实验、并因此而颠覆这两门语言的规则。日语给了李箱一定程度的自由。他阅读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的译文并接受了他们不动感情的风格,用这种风格来处理他本人在帝国下的错位。通过殖民的交流,他吸收了欧洲文化和美国舶来品,从让·科克托到科蒂香水到MJB咖啡。日语是他尴尬的,通往更广大世界的港口,就像英语对英国臣民及其后裔,比如说罗伊来说那样。就像李箱在一个关于一次想象东京之旅的故事中写道的那样,“在拥有一门像我腋下的海洋一样博大的语言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轻易地饥饿。”
最近出版的,由杰克·郑(Jack Jung)、中保佐和子(Sawako Nakayasu)、崔唐美(Don Mee Choi)和乔伊尔·麦克斯威尼(Joyelle McSweeney)组成的三语诗人-译者团队翻译的李箱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集,就有助于我们把握他的全球文集。这本新书也展示了,他是怎样挖掘同时撕破殖民的语法的。他的合成的、超现实主义的词汇描述了首尔的生活,表现了殖民统治下工人阶级的阴郁、时而荒谬的现实。最重要的是,他对东亚和欧洲风格的混合,有助于形成一个从内部颠覆帝国的模型。
李箱原名金海卿,生于1910年,也就是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第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画家,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几个手指后,只好靠帮人理发为生;在生李箱之前,他的母亲还生有两个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李箱就被他处境更好的表叔收养了,表叔没有儿子,就把他当作自己的继承人来培养。李箱很早就表现出制图天赋,并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他的养父担心他会饿死,并敦促他学一门更加实用的学科。他同意学建筑,给自己取了李箱这样一个东亚风格的笔名,并在首尔的殖民政府谋得一个安稳的职位。
身为占领国雇佣的公务员,李箱把他周遭的环境用到了极致。他踏实工作,为建设项目起草计划。他还在下班后设计杂志封面、画画、写诗歌和散文。和当时几乎所有的韩国人一样,他上的是日语学校,并参加了各种要求他用官方语言书写的,官方主持的竞赛。
李箱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要是没有生病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在那个岗位上干下去。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得了肺结核,这迫使他辞去工作,下乡养病。后来,他和一名名叫锦红的妓生(gisaeng)回到首尔,并和她在市区开了一家咖啡馆(茶房),这个地方逐渐变成像双叟咖啡馆那样的地方:一个逃离街上到处都是的日本士兵和国旗的,波西米亚式的避难所。
常在咖啡馆混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包括九人会(Guinhwae)的成员。九人会是一个作家和诗人团体,它的成员都是年轻人,他们用韩语写作,风格多样。这些人包括和李箱一样热爱西方现代主义诗文的诗人金起林(Kim Kirim)(在他最著名的诗作之一中,他把春天描绘为“发光,/瘙痒欲动而/懒惰的豹”)和小说家朴泰远(Park Taewon)(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凭《寄生虫》荣获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奉俊昊的外祖父)。
不久之后,李箱就加入了这个团体,并在余下为数不多的几年里,创造了不少谜一般的、意象式的诗和短篇小说。他的写作经常是像刀一样锋利,诅咒式地描绘了殖民生活的穷困和在精神上的无家可归。
1934年,通过九人会的关系,李箱开始在《朝鲜中央日报》上发表《乌瞰图》,按他的设想,这个系列作品包括30首诗。这个系列作品的题目,是用当时韩国人使用的(现代汉语也会零星使用的)繁体中文写的,取自一个相当于英文的“鸟瞰图(bird’s-eye view)”的常见习语。但李箱用乌鸦的“乌”取代了鸟类的“鸟”并融入了他自己的象征。
这些诗本身甚至放在今天也非常独特,其原本的形式,就像是实验书法合并了数学证明。李箱把文字和修改过的数字和装饰结合到一起,证明了诗人艾丽莎·加伯特(Elisa Gabbert)的论证,即,标点符号(想想艾米丽·迪金森的那些凶猛的破折号)可能是诗的“最低限度”标准。《乌瞰图》的第5首诗是这样的:
一条痕迹表明左右都
被抹除。
大翅│不飞
大眼不见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人在
一个矮、胖的神前崩溃。
能区分燃烧的器官
和溺水的牛棚吗?
接下来是完全达达式的作品第6号:
小鹦鹉[*]2匹马儿
2匹马儿
[*]小鹦鹉是哺乳动物。
啊我-我知道2匹马儿啊我啊不知道2匹马儿。当然我
依然希望。
然后是作品第13号的超现实的整体:
我的手臂在握剃刀时被砍断。我审视它,它呈淡蓝色,看起来
在害怕什么。我以同样方式失去还在的那只手臂,所以,我把
我的两只手臂搭成烛台来装饰我的房间。我的手臂,虽然死了,
看起来还是在害怕我。我爱比爱任何花瓶更爱这些脆弱的架子。
每一行诗的意思都不确定。但放在一起,这些诗表现了一种暴力的荒谬感。
《乌瞰图》也得到了真正的前卫作品应得的待遇:被视为冒犯或威胁。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众所周知,它在1913年首演时引起了一场暴乱)一样,李箱的《乌瞰图》也招来了“作者怕是疯了”的指控,读者纷纷要求停止刊载这个作品。在作品第15号刊发后,在整个作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朝鲜中央日报》放弃并取消了余下的作品。李箱以一连串歇斯底里的叫喊作为回应,这些个回应很适合社交媒体,但他一直没有把它发表出来:
为什么你们都说我疯了?我们落后别人几十年了,你觉得自满没问题吗?谁知道呢,我可能没有足够的才华来成就这件事情,但我们真的应该为我们胡搞乱搞浪费的时间后悔……我费力从我在1931年和1932年间写的2000个东西里选出这30首诗……遗憾的是在这片废土上,我的嚎叫没有任何回音!我不会再尝试做这样的事情了——当然,总有别的法子,但现在,就这样吧。我要潜心学习一段时间,并抽空试着治疗我的疯狂。
李箱一有空就写诗和给九人会的朋友画插图。他试图在市场上立足,但他是个糟糕的(或不走运的)资本家——他的咖啡馆失败了,他和锦红的关系也失败了。
1935年,结核病还没好的李箱两次到还没有工业化的韩国乡下休养、写作。但他这段时间写的文章表达的,是一个书生气的世界主义者对远离城市的哀叹。即便以田园风景为背景,他的修辞还是把城市给浪漫化了:“虫子的声音很大。像舞厅的窗子没关”,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在另一篇题为《无聊》的文章中,他问,“这些村民有希望和梦想吗?我确定他们都希望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那不是希望。那只是生存本能。”(和新文集中收录的许多诗文一样,《无聊》也是在李箱身后出版的,多亏了九人会的努力。)
李箱想要的不只是生存,因此,不久之后他又回到首尔,爱上一个名叫卞东琳的女子,并和他结了婚。1936年,他进入了他最具生产力的一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翼》并搬到东京,渴望见识全球都会。那个梦想,和他的自然之梦一样,并不持久。在和东京的韩国艺术家联系后,他被逮捕并因反日本帝国“思想罪”这样一个模糊的罪名入狱。只是因为他的结核病,他才被释放——但警方也不让他回家。在父母去世一天后,年仅26岁的李箱在东京一家旅馆去世。流言说,他死前曾在病床上要求尝一口柠檬的味道。
从留下来的照片来看,李箱是迷人的,他有一双小巧的耳朵,和卷曲的头发。这位伟大的诗人只是一个穿深黑色学生制服的男孩,或一个穿短袖衣服,领带和吊带裤,叉着手,评判世界的年轻人。要是李箱能活更久,活到从东京回来,再去最初的超现实主义者的家巴黎,会怎么样?
在法国的建筑、咖啡馆、时装和收集了全世界的著作的书店的环绕下,李箱可能会加入实践文类糅合技艺的艺术家圈子——就像他和他的朋友们在首尔试图做的那样,但没有帝国监视的压力。他可能会学习法语和英语,并继续在诗文和油画中扩建他不可定义的、多语言的符码。在这场思想实验中,他甚至可能回到一个统一、和平的朝鲜半岛。
当李箱和韩国在更加阴郁的命运中遭遇的时候,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的诗包含多个可能的世界。在1934年,大约24岁,尚未走出被占领的韩国的李箱写下了《给*白*花*的话*》,一首以被一根不得其所的穗穿透的稻田为背景的阴沉情诗:
1
月光下在你的脸面前我的脸变成一条皮肤我赞美
你的话没出口但像一声叹息它们挠开滑动的纸门
溜进你闻起来像山茶花田的头发并移植了我悲伤
的秧苗
2
漫步在泥地里你的高跟鞋踩出了洞天下雨了洞里
填满了水……
在1931年用日语发表的出自《乌瞰图》系列的《◈两个人••••• 1 •••••,》一诗中,李箱把城市换成了乡下但又换了回来。他在一首简短、刺激的混成作品中结合了西方式的英雄和反英雄。
耶稣基督衣衫褴褛地开始布道。
卡彭为橄榄山的本相而夺了它并继续赶路。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的某个时候——,
在某个教堂霓虹闪烁的入口,一个圆胖的卡彭家族成员在买票的同时
伸缩他脸上的疤。
李箱的作品和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一样超脱尘世。他的诗《墓碑:失踪的妻子》甚至提到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者的“自由结合”:“我的妻子有做出/机械和绝望运动的火箭大腿/我的妻子有蕴含古树精华的小腿/我的妻子有首字母缩写的脚。”在李箱对运动的妻子的描述中:
我的妻子必然是某种鸟。她如此之瘦,几乎没有重量,可她
因为手指上的戒指而不能飞……有时,她会打开窗子
看一眼辽阔的旷野,却从不用她纤细的声音啼叫。我的
妻子看起来至少知道怎样飞和怎样死,因为
她从来不在地上留下脚印……
李箱诗中的女人是介于囚笼与自由之间的鸟。她也是“脸上带妆”的通勤者。“我的妻子每天早上都要出去工作。每天,她都要欺骗男人,哪怕她骗他们的顺序会变”,他这样写道。性工作者还是鸟?无论如何,是超现实的。
已故的学者和法国现代主义的译者华莱士·福利(Wallace Fowlie)写过,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代表“诗人与他周围的真实世界的分离”,一种对一战的艺术反应。李箱看起来也在自己对殖民生活的重负的回应中表达了这种分离。他对风格的选择,可能是在规避帝国审查的同时,传递帝国噩梦的最好方式。“我一直拉,门却不开,因为我屋里的家人快活不下去了”,李箱在《家人》中这样写道。“我像夜里的草塑一样燃烧。我的家人被困在被封印的门里,我不能把自己换进去。”
在《作品选》前言的年表中,杰克·郑指出,李箱和九人会预示了一个名叫韩国艺术家无产阶级联盟(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cio,这当然是世界语)的社会主义作家联盟的出现。KAPF采用的是社会现实主义的而非现代主义的进路:他们的小说突出表现了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遭受不义的穷人和工人无产阶级。这个联盟大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它对标的是欧洲、日本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类似努力,最终,在二十多名成员被捕后,联盟被迫解散。
李箱不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也没有抛弃他周围的世界。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在形式上荒谬,却装满了日常生活:城市里的穷人,不幸福的夫妇,奋斗者,赌徒,猎食的生意人——殖民凝视下的常规角色。类似地,李箱的作品也大量地提到了地标性的建筑和大众市场产品,构成首尔这个以殖民都会(东京)为模型的,被偷走的城市的所有原材料。
但李箱后来又带着喜剧性的严肃,评判了他在去东京前想象的那种现代化的铺张。他在散文《东京》中写道,“我心目中的”带拱门和快速电梯的丸之内大厦“至少有(现实的)四倍大并且要更惊人得多”。在银座商业区(也是中央规划的一个模型),他回忆说,“我去了一座桥旁边的一个地下公共厕所,在排泄的时候,我把我所有吹嘘自己来过东京的朋友的名字都念了一遍。”李箱的诗歌和小说也表达了一种来自底层的、自下而上的批判(虽然形式更加微妙)。《作品选》收录了一篇题为《蜘蛛&蜘蛛遇见猪》的关于蜘蛛男女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也谈到了性别化的劳动、军营城镇中的暴力和赌场资本主义(并通过去掉字与字之间的空间而营造了某种幽闭感)。
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保罗·艾吕雅相信,好的艺术家和工人阶级有着同样的事业。他写道,“名副其实的诗人会和无产阶级一样拒绝被剥削”。“所有不遵从那种道德——为了维持它的秩序和它的特权,这种道德只建造银行、兵营、监狱、教堂、妓院——的东西都包含真正的诗。一切把人从可怕的财富中解救出来的东西都包含真正的诗,那财富不过是死亡的表象。”
李箱可能不认同韩国乡下的农民,但他也在实践他自己的政治。在九人会,他找到了同志,也找到了一个艺术之家,后者和KAPF致力于建设的东西没那么大差别。他去世前的一年,他接手父亲的印刷生意,并出版了九人会期刊《诗与虚构》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比他活得更久的九人会成员在二十世纪中间的那几十年里也没有找到任何后殖民的自由。日本的占领演变为二战,二战又演变为民族分裂和朝鲜战争。奉俊昊的外祖父朴泰远去了北边,也许,是希望到左翼的天堂去做艺术。金起林也一样,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失踪了。
李箱自己则再没有回来。但他的祖国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个由富有的天真汉、镜子、血、山茶花、几何图形、等式、说话的动物、剃刀和失踪的父亲组成的神迷世界。在这些物和符号之下,是数层关乎存在本身的问题,文学学者和批评家权宁珉(Kwon Young-min)近来评论说:“为什么人们要这样生活呢?为什么必须这样写诗呢?为什么一些人要走上这样迂回、突兀的路呢?”对李箱在日本统治下的臣民同胞来说,在母语和被迫学习的语言中,这些问题必然与特定的力量共鸣。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折射在李箱对爱、帝国与城市凡俗的古怪蒸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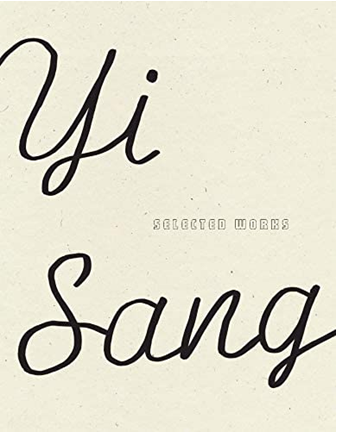
李箱(Yi Sang):《李箱:作品选》(Yi Sang: Selected Works), Don Mee Choi ed., Jack Jung, Don Mee Choi, Sawako Nakayasu, Joyelle McSweeney, trans., Wave Books, 2020, 224 pages, 978-1950268085。
微信版见“海螺社区”: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EyNDQ4OQ==&mid=2657451882&idx=1&sn=7ebc46862865cc68cdb9257a0c7610a1&chksm=bd1d58cc8a6ad1da12229f3f6de625498b33141a8c2dda4f1cc9fba889de09fa25cafba04511&scene=0&xtrack=1#rd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