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看见他们,看见自己 | 围炉 · CityU
对话《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看见他们,看见自己 | 围炉 · CityU ——


“看见他们”。
这是那本教学礼记的序言。
那些年轻的奔走的身影大多在瞬息万变中被湮没,却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基层主干。黄灯以一场教学经历的真实回顾,带我们走入二本学生的成长世界,也隐隐揭开了背后平凡中国家庭的烟火百态,和更多可能性。生存,教育,财富,梦想。焦虑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困境与突围或多或少折射了当代大多数青年的行进姿态。除了艰难,还有一种生命力。本次对话,黄灯老师会结合自身经历谈论话题,或许能带给年轻人们迷惘的内心发问,一些中肯的解答,和自我审视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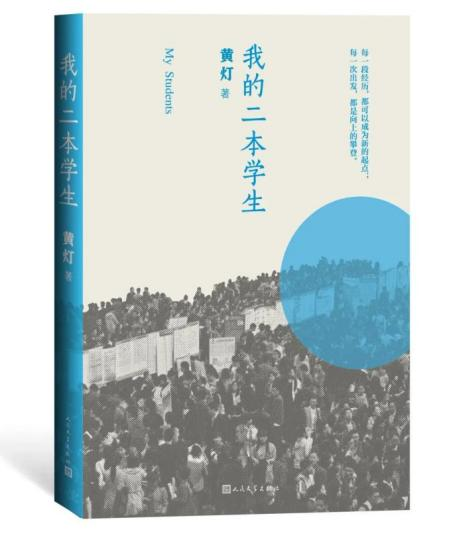
黄灯,湖南汨罗人,学者,作家,现居深圳,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批客座研究员。多年来关注乡村问题,曾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2016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业余写作随笔,曾获“琦君散文奖”、“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主奖,三毛散文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论文奖等。
L = 林睿思
H = 黄灯
1
一种自然的观察
L | 您现在还在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吗?H | 我已调往深圳一年多,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目前主要在带学生做一个非虚构的工作坊。
L | 您是中文系出身的,此前一直任职于财经类院校,那您在教学过程中需不需要调和专业素养和学科知识之间的差异?H | 其实教授的课程和我的专业联系还是挺大的,因为在金融学院时,除了专业课外,我还教一些公共课,这些课程和我的专业匹配度还是蛮高的。
L | 您写《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许多人读完认为它揭示了当代年轻人生存的不易,在引起共鸣的同时,会不会造成某种焦虑,即竞争是残酷的,学历高低就是社会分化的重要依据。H | 我写这本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不是导向性特别强的写作,而是在教了十几年书后,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它来源于一种自然的观察。我到现在为止作品是非常少的,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职业作家。这本书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的记录,至于它在引起共鸣的同时所产生的焦虑,我觉得不应该是作品要回答的问题。不管你讲不讲出这些东西,不管社会上的问题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为有的人把一些真相讲出来,这个焦虑就是他导致的,所以我的作品并没有刻意去引导他人形成一种焦虑的情绪。

L | 是的,焦虑扩张,几乎是当下不可避免的趋势,而非作品的渲染。据数据显示,中国的本科生仅4%左右,而每年高考的二本上线率也不超过30%。也就是说,高等教育队末还有庞大而隐匿的人群。焦虑的背后,出现了一些带有反思性质的声音:谁为其他类似群体发声?您怎么看待这些声音?H | 写书这件事,它是很偶然的。比如说像我写我的二本学生,也是一件并非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对中国的高校老师来说,他们应该具备这个意识,就是尽量把自己所教学的群体的声音传达出去。但是中国现在整个的高校体制,对老师的压力其实也蛮大,很多老师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没有心思去观察自己的学生,更不会把他们写出来。因为这些文字本身属于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观察,对自己教育经验的回顾,在整个评价体制里面,并不属于论文课题之类的学术成果。所以其他老师不写也能理解。但是写的话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像我的话,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可能这在高校里面是很少,也很另类的了。
L | 那么学生对于您用成书的方式展现他们的人生片段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您现在还和他们保持联系吗?H | 其实我在上课过程中就提过这些,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记录你们的故事。好多年了,我一开始是想拉着学生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我希望学生写他们自己,然后老师也写学生,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对比。但是最后学生那部分的话始终没能做成。最后只有两三个学生写了,也不足以出一本书。事实上我本身积累的材料,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多,可以说,书中仅展示了一小部分。我书里写到的学生是我比较经常联系的。中间有几届学生交往比较少,比如说07级到09级,那时候还没有微信,交流就不那么方便。他们毕业后就更难追踪了,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仍保持联系。
L | 这些学子对当下高校内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H | 这些二本学生其实是很能接受竞争的,他们基本上从一进校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到底能不能扛住竞争呢?这就属于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对竞争是习以为常的,所以我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很坦然的,当然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L | 也就是说,他们接受竞争,但不会因为竞争而过分焦虑,这可否理解为在高压的竞争型社会下与自己的和解,在肯定自我的同时尝试接受自己的某些平凡。H | 这可以算是一种和解。我教的学生里面,大部分都挺淡然,确实很能够接受自己的现状。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孩子很有野心和想法。我在广州待了将近20年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广东,所以基于我自身经历,这也有一定的地域关系,从整体上看,这边的学生心态更平和一些,没有太多的抱怨,脾气也没那么激烈。他们的商业意识很强,特别能够用商业的原则来理解现实。我以前也在武汉、湖南读过书,观察了不少地方,这是他们跟内地学生一个很大的差异。而且他们认为就业带给他们的压力,至少就我观察到的现实是肯定有的,但也没有现在网络上渲染得那么强烈。那这本书所要呈现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呢?主要是孩子们的境况和过去相比越来越难了,倒不是说就没有活路了。


2
选择和成长
L | 与过去相比的话,还有分析表明贫富差距正在从暂时贫穷走向跨代贫穷。“寒门出贵子”从您那个年代到现在,发生了哪些改变?H | 以前的教育基本上是顺其自然的,外部环境不会刻意为之。因为当时整个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如现在,小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在当时,本身具备较高素质或者身处较重视教育家庭的孩子比较容易成才。但是现在的话大家普遍都重视,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以前的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特别小,都是正态分布的。我当时读的高中,只是一个小县城里面很不起眼的一所中学,但是它在两年之内出了三个状元。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背后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推动,师资之间的流动变大。像我父亲一辈子在乡村教书,从来没有调过单位过或跳槽,但是现在人才都是流向资源丰富的地方。乡村中学也因此没落。
L | 您长期一线执教,能否讲讲目前国家政策帮扶贫困学生的情况怎么样?H | 具体政策我是不太清楚的。我平时更多接触的是教学方面,比如学科建设,专业培养之类的。但我平时也跟辅导员交流过,目前了解到的奖学金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国家确实在想很多办法来平衡教育资源公平问题,比如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变高了,无息贷款也很多。现在很少会出现因为经济原因导致学生失学的状况了。
L | 在您教过的学生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粤西及内陆山村,他们毕业后会选择返乡吗?H | 返乡的话,有几种情况,有一些是继承家族企业,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考公务员,回到自己家乡的县镇里,或者是公办学校。真正回到农村的其实很少,基本上没有。现实点来讲,因为农村没有就业的机会。
L | 您如何看待大学生去做乡村建设?H | 我从来不会反对学生去做乡村建设,比如支教。短期的志愿服务有点类似于实习,这是学生时代一个特别好的历练。我鼓励他们为社会作贡献,我自己也做乡建做了很多年,但是我不会用一种比较空洞的理想主义,鼓励他们在自身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去做志愿者。我的个人观点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首先解决生活问题,承担自我和家庭责任,而不是还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就去考虑如何回报社会,这是不现实的。我觉得改变社会,那些占有资源,更具话语权和能力的人是可以付出更多的,但是对于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分鼓动他们去付出,而是应先让他们安顿下来,慢慢成长起来。等到内心充满力量,不会陷入太多的纠结和迷茫,也拥有更多能量了,这时他们如果愿意去做志愿活动,我是非常赞成的。
L | 支教本身是好的,但现在也确实有一些大学生以投身乡建来逃避现实竞争,久而久之甚至陷入一种自我感动。H | 是的,所以我一般不会轻易鼓动我刚刚毕业的本科生去做乡建。对于一个年轻大学生来说,做乡建很容易被误导为一种激情式的理想主义圈。因为现在有些老师本身过于理想主义,可能会鼓动自己的学生去参与,这不仅会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还会增加家庭负担。我目睹了很多大学生,在这种氛围的鼓动下跟现实越来越隔膜。比如有一些孩子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对现实有点畏惧。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他可能就会选择去做志愿者。志愿者虽然收入不高,但可以帮助你暂时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只是,如果他是以逃避困难为隐性初衷的话,那么在这种弥漫理想主义氛围的环境里呆得越久,以后就越难进入现实,这种志愿活动也不可能长久。
我个人觉得大学生应该利用刚毕业的那几年,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到社会最真实的一线去探索。通常我会建议我的学生如果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就留在这多去锻炼下。如果回去,能够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你愿意回去也可以。当然了,如果对自我的了解非常清醒透彻,且又具备较强的能力,投身乡建同样无妨。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基于他们有一定的经历,自我认知达到一定高度,才做出的抉择。大部分孩子还是得谨慎一点选择。先把自己养活,再去研究怎样奉献这个社会。
我一般会更加支持他们去接受现实的挑战。在现实中历练其实比做志愿者要难得多。
L |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刚刚进入大学就被告知各种进入社会后将面对的压力,有人说这是一种很实际的提醒和促进,也有人认为不应该过早让他们对未来产生恐惧和压迫感,您怎么看?H | 现在大学生一进大学基本都会被辅导员或者师兄师姐灌输这种观念,传达这个氛围。而我会站在老师的角度,提醒他们,不必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焦虑也没用的。进入大学的一个核心目标并不是为了应付就业,而是要使自己通过高等教育真正获得成长,我认为这个比单纯解决就业更重要。因为求职本身是偶然性很强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所掌握的基本知识,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L | 您对您教过的“成功”的学生的定义是什么?H | 我觉得一个孩子只要通过大学教育,能够在社会立足,在我眼中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要不漂泊动荡,内心不安定,不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能够从事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哪怕只是一份很简单的工作,这就已经很成功了。不需要要求他们去做那些很崇高或者达成难度很大的事,这个也不现实。
L | 那您觉得通过大学教育,学生最应该获得的是什么?H | 我平常经常强调专业基础要打好,即使你第一份工作没找好也没关系,还可以考研。另外,你要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让自己慢慢地社会化,不要总是停留在学生思维。而这在大学里面其实是蛮匮乏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学教育,只是在强调一些很表象的东西,比如职业规划之类的,这些也并非不重要,但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学生与社会对接的能力。很多学生非常希望有人指导他,但有的老师缺乏观察能力和行动力。比如说,我发现不少孩子还不会写邮件,缺乏基本的礼节,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很不好的。老师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提醒他们,教他们怎样落落大方地与人交流,不要自卑、畏缩,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很坦然地面对一切。这些都是需要人提醒和鼓励的。
L | 我们常说要开拓眼界,但眼界这个概念本身就受客观条件制约,比如学习生活的环境,您提到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塑造“完整的人”,那么您认为“眼界”的高低是否应作为其衡量标准。H | 我认为现在的教育倾向于单向度地强调学生的某些方面,比如说中小学阶段就是分数,大学阶段就是绩点,就是那些看得见的KPI层面的东西。而我其实更注重学生精神成人这一块。这些大学生都是年轻人,价值观还没有定型,精神也还不成熟,但学校往往会忽视这些。所以我这里所谓的完整的人,至少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是专业素养方面的。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至于眼界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实上一个人进入大学后,他的认知相对以前来说,就自然开拓了很多。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故意为之或一蹴而就的。有些孩子来自很偏僻的山村,所以其实他们只要考上了这所大学,就意味着他们的眼界已经打开了很多了。当然了,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考到北大清华的孩子肯定又不一样的,是吧?因为他们接触的资源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其实这些都没有高下之分。往上拓宽视野固然重要,了解一个社会的最基层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很有助于一个人的成长。一个名校毕业的孩子,如果总是身处上流,没有机会接触基层的话,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这个眼界的开拓是双向的过程,不应该只是一味向上,国际化和在地化都很重要。我接触过一些在国外顶尖大学留学的学生,有时候跟他们交谈,我就会想,你们要是有机会到底层世界去耐心呆一段时间,对你们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这些孩子的知识结构很好,对外交流多,但是很多对中国的真实现实缺乏认知,这一点是蛮遗憾的。我认为让一个孩子从那一波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去了解基层。当他具备了国际视野后,如果能再去了解基层的话,他的感知就会丰富很多。包括对学术的敏感度都会不一样。当然我带的这些二本学生,如果有机会去接触更多国际化的事物,对他们改变也会很大。这是一个不断流通的过程,因为现代人非常容易相互产生成见,所以这种突破隔膜的能力很重要。这必须要亲身观察,才是可靠的。因而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尽量客观地把我的观察表达出来。
3
课堂外的摸索
L | 您在书里提到了“导师制”,您能谈一谈这种独创的教学模式带给您和学生的体验和影响吗?H | 因为我以前博士是中大毕业的,中大的本科生是有导师制的,导师主要是硕士和博士生。所以我以前在中大读书的时候,就带过本科生给他们改作文之类的,交往还蛮多的,因此受到了启发。后来我在金融学院上课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孩子很想学习,但缺乏机会。那时我就在想,不如把中大的导师制迁移过来。相当于是君子协定,你们愿意学,我就愿意带,没有经费支持,也不计入考核。当时学生管理相对松散,但因为他们都是自发性的跟学,所以还蛮认真的。生活上面肯定相对别的学生来说会多一些。因为不住在学校里,我会偶尔周末邀请他们过来玩,带他们到中山图书馆,中大校园里面去走走,或者到广州的老街上去逛一逛。平时在学校有空的话,也会每个星期都跟他们见面,带着他们读书,给他们改文章。这些孩子很听话的,可爱学了,经常发好多文章给我看呢!
L | 这种模式后来有尝试在其他院系或学校推广实践吗?H | 这个没法推广的,如果推广的话,就变成了对老师的一种强制行为,校方也必须投入资源。所以是不可能大面积推广的,我们也最多是在小范围内深耕。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当教研室主任,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达成了共识,就在教研室内做了很多年,也有很多老师参与。



看过《月亮与六便士》,你相信理想主义是存在的,要不顾一切去追寻,然而在《人生的枷锁》里,毛姆却毫不避讳地驳斥了这个想法——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生活的懦怯的退缩。他没有力量去奋斗,所以就把这种奋斗说成是庸俗的。
那么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什么?或许是认清生活本质后的坚持搏斗,是先安身,后立命。走出高等教育的屏障,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答案告诉我们必须成为什么。黄灯试图从普通生命节奏里挖掘隐含的人生真相,通过看见个体的努力,去理解这个时代。那些温和行进的身影里,或许也有相似的故事。

文 | 林睿思
图 | 来自受访者和网络
审核 | 尹昕儒
微信编辑 | 吴雨洋
Matters编辑 | Marks
围炉 (ID:weilu_flame)

围炉近期在举办读书会,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扫码报名!(添加时记得备注想参与共读的书目)
以下为各个读书会群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理解人性》(6.18-7.10)
《艺术的故事》(6.18-7.16)
《荆棘鸟》(6.26-8.7)
《局外人》(7.2-8.7)
《妮萨》(7.2- 7.31)
《阁楼上的疯女人》(7.6-8.20)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