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 哲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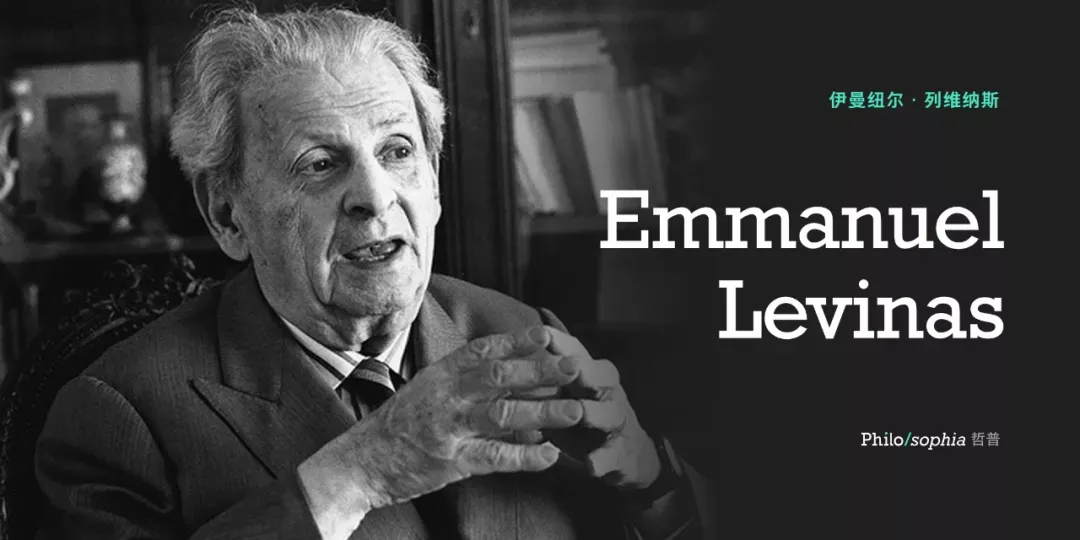
「本文于 2020.7.12 原载于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
作者 / 移山
笔者按:德里达曾经评价,列维纳斯的思想有如海浪拍打沙滩,愈加不懈地循环往复。笔者才疏学浅,只希望这篇文章能让读者感受到海风的咸味儿。若有疏漏谬误之处,万望指教。
感谢埃及人、木风和 zxx 在本文修改中提供的帮助!
1 生平
它被关于纳粹恐怖的预感和记忆笼罩着。
DF, 291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Emmaneul Levinas) 在 1905 年生于立陶宛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乌克兰上中学的时候经历了俄国革命。1923 年,列维纳斯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开始关注现象学,并结识了终身好友布朗肖。1928 年,列维纳斯到弗莱堡大学参加胡塞尔的讲座。这不仅对他的哲学生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现象学引入法国、启发萨特等哲学家的契机。当时他对海德格尔的评价甚高:
马丁·海德格尔是胡塞尔最有原创性的学生,他的名字现在是德意志的骄傲。
OHL, 105
列维纳斯此时愈是仰慕海德格尔,日后他的震惊和失望愈深。1933 年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党,对他有如晴天霹雳。他立即中止了关于海德格尔专著的写作计划,并于次年发表文章,对希特勒主义进行哲学分析。

1939 年,二战爆发,列维纳斯加入法国军队,作随军翻译 。他于次年被俘,作为法国军官被送进战俘营,而他在立陶宛的家人几乎全部被纳粹杀害。亲身经历的恶将对他的哲学思考产生深远影响。在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变得更加不可原谅的同时,海德格尔哲学和政治的联系成为了列维纳斯反思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之切入点。另一个问题是,在纳粹的罪行以后,重建伦理学的可能性:
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谈论绝对戒律吗?道德失败之后,我们还能谈论道德吗?
PL, 176
战后,他担任东方以色列师范学校校长,并开始发表原创性著作。1951 年的《存在论是基本的吗?(Is Ontology Fundamental?)》,批判了把存在论置于核心的海德格尔哲学。1957 年后,他每年进行犹太法典塔木德 (Talmud) 讲座。1961 年的《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是列维纳斯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974年,他出版另一部重要作品《异于存在或在本质之外》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几十年间,列维纳斯著述颇丰,直到 1995 年与世长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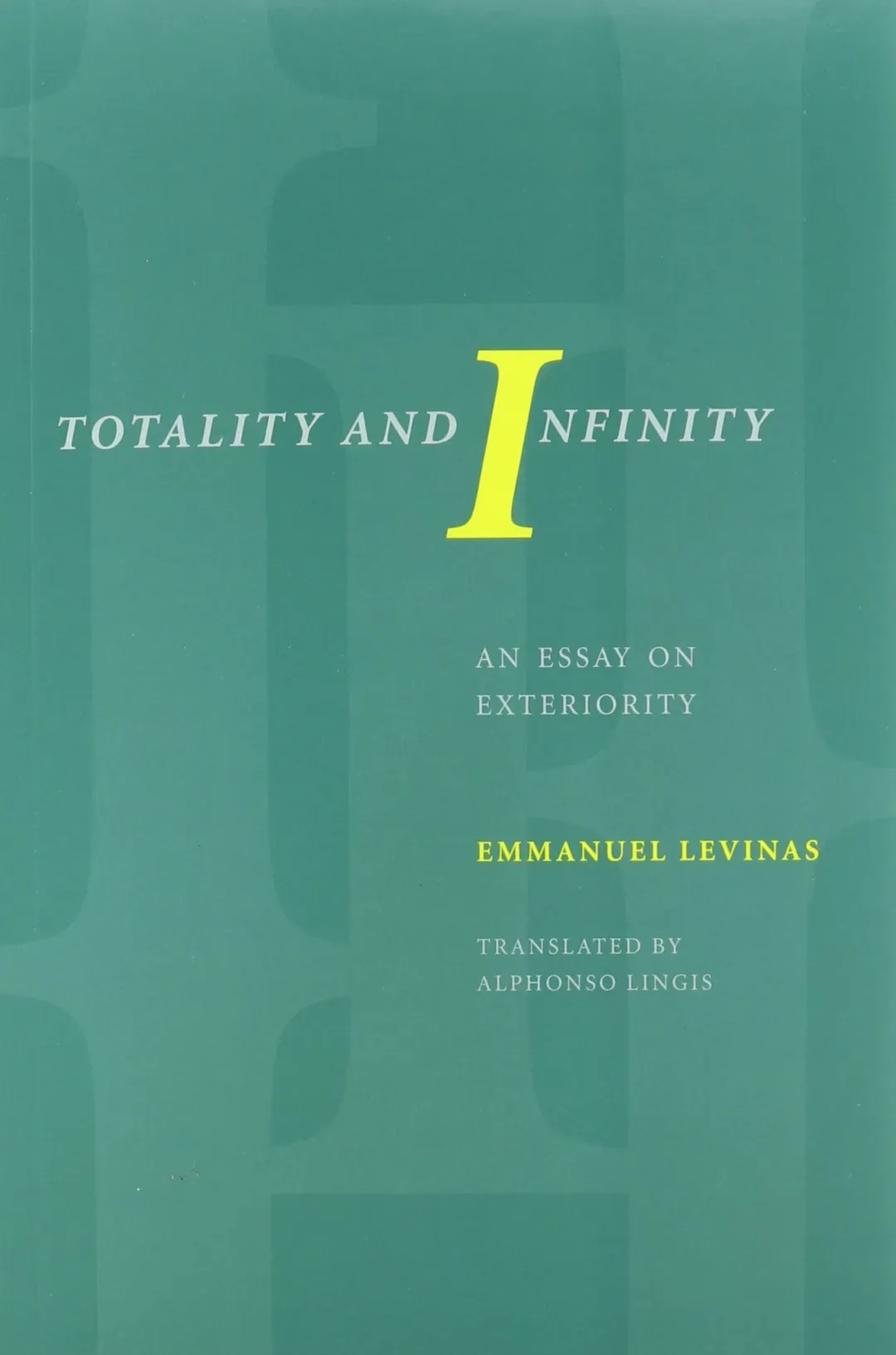
2 总体与无限
写在前面
成书于 1961 年的《总体于无限》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海德格尔问题。如生平节所述,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海德格尔在二战中与纳粹的共谋和奥斯维辛的残酷揭示了西方存在论哲学史长久以来的弊病,也开启了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思。列维纳斯回溯到了巴门尼德的一元论 (monism):巴门尼德把存在视为唯一的和不变的。列维纳斯把巴门尼德一元论认作西方哲学追求总体齐一的精神,而忽视甚至消灭他者 (the Other) 的开端;而把海德格尔认作存在论哲学的集大成者。
他者问题。总体 (totality) 被列维纳斯用来描述西方哲学的特征;无限 (infinity) 被用来描述描述被西方哲学传统所压制的他者。《总》的意义是离开巴门尼德式本体论,离开「海德格尔思想的气候」,反对以追求真理为名的齐一暴力,进入一条新的以他者为中心的进路,同时也肯定基于他者的多元思考。
在肯定他者的哲学中,如何保证他者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总体的开端?只有从“我”开始,证明我并不是能够被同化的主体。以同一为特性的自我 (the self) 处在其未认识到他者之前的享受 (enjoyment) 中。外在性 (exteriority) 与自我的主观性 (subjectivity) 和与其共生的内在性 (interiority),导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离 (separation),而分离是自我的意识无法将他者同化为总体的一部分的原因,也是他者不会反而成为同化自我的另一种总体的起点的原因。只有以自我作为端点,才有可能响应他者之脸 (the Face of the Other) 的召唤。他者之脸让自我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与自发性 (spontaneity) 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以及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以及责任的性质。
何谓总体?
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总体是西方哲学的共性。总体又有两个特征:
1. 总体把一切都变成某种系统中的一部分。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如果我以总体化倾向来主题化或者概念化他者 [TI, 43],剥离他者本身的他异性,把他者还原成总体的系统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便通过主题或概念占有了他者。
2. 总体用普遍的中性 (neuter) 吞噬个体。这意味着,在总体当中,个体变成了中性的、非人的普遍力量(比如存在或理性)的载体。比如,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化史观中,自我的精神与外在世界中异己的成分相遇,前者将后者概念化的同时,调和两者之间固有存在的任何不同或对立,从而达到总体。
上述两种特征之于个体的共性是,个体的意义仅仅是在总体中体现的。
何谓无限?
列维纳斯从笛卡尔《沉思》第三篇中借用了无限的概念。对于笛卡尔来说,在怀疑包括自身存在的一切之时,我发现我对于上帝的概念包括其无限性 [PWD, II, 28-31]。在他的经院哲学背景下,笛卡尔假设果不能比因有更多的客观现实 (objective reality)。我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因此无限的概念的原因并不来自我,而是一个真正无限的存在。对于笛卡尔来说这无限者是上帝;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无限的概念的意义并不是证明上帝存在,而是显示纯粹的外在性不能够还原到我的内在性之中 [TI, 210-211]。这种纯粹的外在性来自于他者,因此列维纳斯说:
无限性是超越者的特性;无限是绝对的他者。
TI, 49
忠于列维纳斯——「我们的分析受一个正式结构引导:我们当中对无限的概念」[TI, 79] ——下文的第一条主线是围绕着无限展开的。内在性与分离让我能够有无限的概念,因此我们要先考察「我」的享受和渴望;而存在总体被他者的无限性超越。由此我们引出显现了无限的他者之脸。他者之脸将带来理性和自由的全新定义。最终我们将讨论生育、死亡与无限时间的关系。下文的第二条主线是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的对比。由「生平」节所述,海德格尔是列维纳斯重要的思想背景,也是他面临的哲学命题。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分歧之处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列维纳斯。
3 我,存在者
存在总体
西方哲学最常见的形式是存在论——用一个中性的词语把他者还原成同一,从而保证对存在的理解。
TI, 43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做出了存在的 (ontological) 和存在者的 (ontic) 层面的区分。存在者的层面关于存在着的东西,比如镰刀和锤子,瀑布和森林;也关乎关于存在者的概念,比如数字和形状;考察这些概念本身的学科是数学和以物理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存在的层面关乎「存在」;调查关于存在者的概念属于存在的层面,比如调查数字的存在和镰刀与锤子的存在的区别是存在层面的问题。数字的存在和镰刀与锤子的存在不一样,所以有存在本源的意义之问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 of Being)。试图表达这个问题是基本存在论 (fundamental ontology) 的任务。
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以某种本原为核心的存在论预设了自身的绝对优先地位,「存在是本源,是开端,是原则。一切都奠基于存在之上,都可以还原为存在。」[朱刚, 8] 不管我们有没有像海德格尔所说那样忘记关于存在的问题之源,存在是中性的、非人的、无声的 [DF, 206-7],没有什么反对作为总体的存在,没有什么给存在做判决。当海德格尔决定存在的比存在者的层面更加原初而重要之时,他就已经决定了让存在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属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 [TI, 45]。
虽然海德格尔承认共在 (Being-with) 作为此在 (Dasein) 在世的必然,但把其描绘成此在沉沦 (the fall) 的先决条件。所有的他者都是他人 (the They) 当中的一员,他人的平庸 (averageness) 拉低了 (levels down) 存在的所有可能性 [BT, 165]。这是在说两点,1. 此在过度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同异来定义自己;2. 此在的所言所行与他人趋同。这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定义是,此在是其存在成其问题的存在 [BT, 69]。而只有在直面这个问题时,在试图为存在给出自己的解答时,此在才有达到其本真性 (authenticity) 的可能。1. 的问题在于,如果此在把他人作为参考系,比如,「我想给出海德格尔哲学的全新阐释,和别人都不一样的阐释!」,我已经是在在用他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向他人的基准与规范投降了。2. 的问题在于,如果我和他人趋同——看一样的电影、刷一样的社交软件、对一样的梗发笑——那我是谁?此在活在他人的影像之中。在两种情况中,他人都是此在本真性的障碍。此在达成其本真性的过程就是拒绝他人,找到自己存在的诠释的过程。
理清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哲学思路后,我们将转回列维纳斯,并逐渐展示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于何处迥然不同。首先,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中,真正被忘记了的,不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本源意义之问,而是不同的存在者之间不可还原为总体的一部分的关系。后者先于前者,掌握着前者 [TI, 47—48]。而后者的起点是自我,所以我们转而考察列维纳斯对于自我的现象学分析。超越存在总体有三步:
1. 自我的享受与分离;
2. 自我产生渴望;
3. 自我遭遇无限,即绝对他者。
享受、栖居与劳作
我们享用好汤、空气、光线……
TI, 82
在对生活的反思之前,生活本身已然发生了。不同于胡塞尔所认为的,即我与事物的关系是认知的,在事物成为认知对象之前,我首先是在享用它们——并不是喝汤的想法,而是喝汤本身;并不是晒太阳的想法,而是晒太阳本身。享用的过程也与达成什么目标无关。

这是对海德格尔对于此在日常分析的反叛——根据海德格尔,此在把自己的在世理解为一系列筹划 (projections) 和目标,使用工具达成,比如我在建房子的时候使用锤子 [BT, 95–102]。这并不错,但即使对于海德格尔式的筹划型此在,也有更加原初的体验——达成目标中享受的过程。我进食而得以生存不假,但是在进食的过程中,我在享受食物。当然,不是所有自我享受的东西都能吃,但吃最具体地表现了海德格尔的筹划和工具化世界观的不足。
生活……不是对于这种生活的存在论的操心 (Sorge)。……生活是对生活之爱。
TI, 112
然而,生活之爱、生活之享受带来的幸福很可能灰飞烟灭:俗语讲,吃了上顿没下顿;列维纳斯讲,「幸福始终要靠运气。」[TI, 144] 我需要未来还能够享受的保障,幸福的保障。这是家的作用。我可以暂时避免外界对于我享受的威胁,并且存储我享受的东西以及我劳作的成果来保障未来的享受。但这不代表家只是功能性的庇护所,另外一种工具化的存有 [BT, 116]。对列维纳斯来说,家是家。它代表了我在大地上的位置,是任何其他活动的开端。
自我与分离
我们已经发现,列维纳斯的自我是具身的 (embodied) 自我,可以饮食、劳作和栖居——这些都是自我的「家政式实存」。
有必要作出两种「他者」的区分:在家政式实存中,有能够被我同化的对象型他者 (autre),可以使用、享受和认知。比如,面包和酒可以被我消化吸收,风景可以被我享受,一般事物可以被概念化和主题化地认知。它们都属于他者 (autre) 的范畴。他者 (autre) 甚至包括能够丈量的星空 [TI, 37],因为我可以概念化地认知它,让它成为我知识的一部分。与之相反,不能够被同化、不可还原到我的概念之中,即不可被我的内在性掌握的他者 (Autrui) 是拥有伦理意义的他者。
在「家政式实存」当中,自我达成了分离。分离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完全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距离。由无限性的定义「无限性是超越者的特性」[TI, 49],分离可谓无限性的具体表现。
由此可做一个重要的推断:分离是积极地而不是被动达成的。被动达成的分离意味着,自我意识可以来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式对立,或是与自我对自身表象 (representation) 的认知关系。但实际上,在对自我任何概念化和主题化的认知之前,自我已经在享受中积极地达成了自足。分离在我享受的心态,在我的唯我式幸福中达成 [TI, 62]。也就是说,自我不是通过否认他者而确立自我的,自我和他者不是正题和反题 (thesis and antithesis)——如果是这样的话,两者又会被黑格尔式的总体吞噬。
绝对的他者给予了我对于无限的概念,但这只在我已经是一个分离的自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列维纳斯写到,「本书为主观性辩护。」[TI, 26] 因为主观性保证了我有我的享受,和享受带来的分离,而这是我与他者共同存在的方式。「内在」保证了他者的外在性,也是他者的无限不会成为另一个总体、把我吸收的先决条件。因此列维纳斯不指责享受。享受让分离和无限成为可能,享受是超越存在总体的第一步。
渴望、形而上学与绝对他者
渴望是来自于无所缺乏者的需求。
TI, 103
超越存在总体的第二步是渴望。渴望与需求不同。需求产生于缺乏,如果缺乏被解决了,需求也就消失了。也就是说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如果我饿了(对食物产生需求),则吃饭就可以满足我。但是渴望是不可满足的。因为享受中的我是无所缺乏者,无所缺乏者感到的渴望是不可满足的,否则这渴望其实就是需求了。真正的渴望是我在自足的享受能感觉到的「对于绝对他者的渴望」[TI, 34]。列维纳斯断然道,渴望的行为不是「消费,抚摸或礼拜」[TI, 35]——声色犬马无法满足渴望,宗教也不行。这就把渴望的境域划离了自我的享受和爱欲,也把渴望和宗教体验区分开来。我们的问题域不是神学的,而是哲学的。渴望的存在促使列维纳斯对「形而上学」,这个哲学的传统词汇,作出全新的定义:
[形而上学] 转向「别处」,转向「别样」 [的维度],转向他者……形而上学的渴望朝向完全别样的事物,朝向绝对他者。
TI, 33
它从我所熟知的世界(我的享受,我的在家)出发,转向我一无所知的世界。而我——渴望者、形而上学者——与绝对他者的关系并不源自我的缺乏和需求,因为我在渴望之前,本已在自足的享受中了。虽然说需求和渴望都是我感觉到的,但是需求从主体开始,渴望从「客体」开始 [TI, 62]。这不是在回到现象学之前的主客体二分,而是在确立渴望是由被渴望者所引起的。它不是我所缺乏,而是我所向往。渴望的维度由绝对他者打开。

我们还需要把渴望可能带来的感受与幸福作出区分。在分离中,在唯己式实存带来的享受中,我无疑是幸福的。又因为分离中接触到的他者 (autre) 都是可以被同化的,我对于不可还原的他者一无所知。但是不可还原的他者唤起的渴望可以说是「幸福者的不幸」[TI, 62],因为渴望不是为了享受而渴望的:它超越了幸福,也可以牺牲幸福。
另外,渴望是不能吸收与同化被渴望者的,因为其绝对他者的外在性不能够被我还原成我内在概念中的一部分。满足这种描述的他者,不是可以被同化的他者 (autre),而唯有作为他人的绝对他者 (Autrui)。绝对他者能够完成超越存在总体的第三步。由此,我们引出列维纳斯哲学的关键概念:他者之脸。
4 他者之脸
无限通过他者之脸显现……
TI, 199
无限是超越我的内在性的,因此没有什么足够的概念能够让我掌握它。他者之脸超越了我通过表象 (representation) 来进行主题化和概念化的存在论范畴,这是无限超越了存在总体的时刻。我们能用来定义的词汇都还是在存在论范畴里的,但他者之脸不在这个范畴中。所以,我们不可能直接定义他者之脸,只能从「他者之脸不是什么」出发。首先,他者之脸不是脸,虽然用词让人禁不住这么想。它不能够被看到和抚摸,不能化作图像,不能被拥有和操纵 [TI, 190, 194]。它不是具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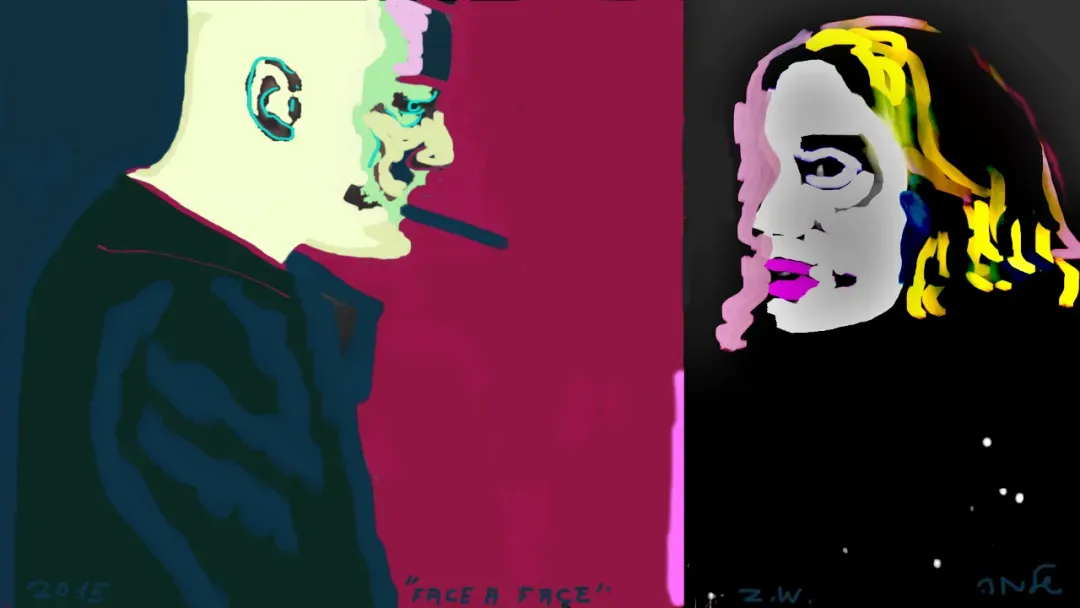
列维纳斯迂回地说,它是「一个显现但仍然缺席的现象」[TI, 181]。我们能够掌握的,是遭遇他者之脸时的现象。它是「外在性或者超越性之光」[TI, 24],这个比喻很特别,因为列维纳斯一般来说很反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视觉比喻,因为视觉,在把一切都变做我可认知和掌控的表象 (representation) 时,把外在性与内在性等同 [TI, 295],但是他还一反常态地说过「伦理学是光学 (ethics is an optics)」[TI, 23, 29]。把这些放在一起,伦理学就是研究他者之脸带来的外在性或超越性之光的现象学。这是怎样的现象呢?
他者向我呈现 (present) 自己的方式,超越了我对他者的概念,我们称作脸。
TI, 50
需要注意的是,脸本身不是现象。他者的被给予性 (givenness) 不是通过现象的表象 (representation) 而是呈现 (presentation)。前者是我对他者的概念化,而因为他者是无限的,我的概念化注定是失败的;后者是来自他者的,对其自身的呈现,是他者的表意 (signification)。因此它是在我认知之外的表意。
在一次采访中,列维纳斯解释了脸的概念 [OHL, 243-244]。通常,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和我们思考人的方式没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他们的性质或特征来思考,这是一种通过表象的思维方式 (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比如这个人是教授或者警官,是某个人的姐姐或者儿子。但是脸代表了独立于任何上下文的表意:「脸自成其义。你就是你。」他者呈现自身,我的诠释 (Sinngebung) 不是表意的条件,而恰恰是在他者表意之后才成为可能的 [CCL, 68]。
「呈现为他者就是表意。呈现为表意就是说话。」[TI, 65-66] 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语言:「脸说话。」[TI, 39, 66]。在对话中自我与他者仍然是分离的,因此语言保持了他者的超越性,我和他者不会被总体化。而对话进行的事实,自我在倾听他者的事实,意味着自我从封闭的享乐和栖居中探出头来,与外在性之光相遇;也是统合存在者的总体被无限超越的时刻。我不再是单独在世的了——他者要求我给出回应。
他者的话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并不是每一次对话都有外在性之光。那么,他者对我说了什么样的话呢?
……原初的话语:「汝勿杀。」
TI, 199
「汝勿杀」中的「杀」是什么意思?须知谋杀和别的行为不同。不管我如何试图通过我的认知或者劳作同化他者,这些都还是不完全的否认,因为我还在试图理解或使用他者。但谋杀是绝对的否认。它还是注定失败的否认:我可以通过谋杀消灭他者的肉体,但因为他者之脸不属于具象或表象的世界,我无法通过谋杀来消灭它。我仅仅能够有暴力的愿望:「他者是我唯一能够希望杀死的存在。」[TI, 198] 但是在谋杀的徒劳当中,能够在我的杀意之前呈现出「不」的他者,不是通过强力反抗,而是通过其不可预测的反应,通过他者之脸,对我有权柄——他者标记了我随意取用和认知的自由的终结点,和我暴力的边界。他者也标记了我责任的开端:
他者之脸开启了最初的对话,第一个词是责任。没有任何“内在性”能够逃避这种责任。
TI, 201
要理解列维纳斯所说的责任,我们必须先了解他对理性与自由的批判。
5 理性、自由与责任
理性总体
列维纳斯并不是全面否认理性的,但要求我们试想一个由完全理性的存在组成的社会,一个理性总体。「一个完全理性的存在该如何和另一个完全理性的存在对话?」[TI, 119] 他们拥有同一个声音——理性的律令——而不是来自个体的不同的声音。须知理性是普遍中性之一例,理性的总体会吸收任何「非理性」异见,而导致两种暴力:将个体毁减成理性的传声筒,理性之「物」;为了同化而征服任何尚未被纳入理性系统的异己个体 [TI, 302],也就是战争。理性没有也不允许复数,可社会是由复数的人组成的。因此理性不能够为复数的人提供伦理 (与道德区分) 的基石。

理性的另一个作用是为自由做辩护。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由常常被当作目标,因此自由的自发性不被质疑。自诩不证自明的理性总体中囊括自由,自由被当作正义的基础。以自由为目标的政治理论把正义建立在所谓「自由」的最大化上 [TI, 83]。比如,自由主义中的每个个体仅仅是自己 [TI, 120],自由是自己的自由。理性在两个层面作用:一是作为唯一的声音来掩饰其理论隐含假设的无根据——每个人的自由都会威胁到别人的自由;二是在理论展开的层面上使用理性调和我和他者之间的自由。以这种孤立的自由为普世性的真理,总体的力量来自于在思想的前提假设阶段就孤立个体,以期其漠视他者的默认设置 (享乐与栖居) 反哺总体,奉自由之名,行暴虐之实—— 「同一的帝国主义是自由的全部内涵。」[TI, 87] 我们在此在的本真性那里看到的,在理性总体中以自由的名义出现:一旦存在者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忘记了无限——就会被总体吸收。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列维纳斯并不是反理性或者反自由的。由于总体中不加反思的理性和自由和战争和暴力相关,他选择反思理性和自由本身,以试图给其找一种辩护 [TI, 302]。若是无可辩护的,就需要赋予理性与自由全新的含义,来使其正当化。
语言即理性
……语言不仅仅为理性服务,语言即理性。
TI, 207
如果要确立的理性的新定义不能是中性的和非人的,理性就必须建立在对多样性的承认上。在这个理性的新定义中,存在者是多样的,他者不是我的副本 [TI, 121]——这是我们在分离的论证中所证实的,而现在这个结论的意义显现了。至少要有两个不一样的存在者,对话才是可能的,所以语言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体现。因此作为语言的理性是多元的理性。
对话有两个方向:他者对我和我对他者。
在他者对我的话中,有他者对我的教授。来自于我之外的启示能教授我本来没有的东西,而不是像苏格拉底在《米诺篇》中所做的那样,唤醒我之中本来就有的;因此被教授不是在循循善诱的发问中回忆 (recollection),而是首先被质疑:
我们把他者的在场对与他者之脸共存的我的质疑叫做语言。
TI, 171
从我对他者的话中,我要对他者的质疑作出回答。主题化和概念化不再是对他者的总体化倾向,而是把我通过享受所占有的由他者 (autre) 构成的世界,通过主题和概念所达成的表意,作为「第一次捐赠」献给他者 [TI, 173]。我对他者的回应是把我的世界公有化。公有化不是去特征化或总体化,因为我的内在性是不可能被总体化的。在公有化中,我曾经的享受被奉献正当化了。
自由即责任
「我们把他者的在场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叫做伦理。」[TI, 43]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这和上文涉及到的对于语言的定义十分相似。又考虑到他者教授我,引文的意义是,作为第一次教授,他者之脸将通过对我自由的质疑教给我伦理的意义。
真正的自由开始于自发性被质疑,乃至我能够在他者面前感到愧疚,感到自己的「不能」与「不配」的;甚至感到自己的自由是谋杀式的 [TI, 84]。这对应着我能够意识到在现行的总体中,我的自由是以他者为代价的:此处「他者」指代他者本身,包括他者的无限性、他者的自由、他者的生命。因为我在第一次被他者之脸拷问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成为了总体的一部分,如何沉默着成为维持他者沉默的帮凶,更衬总体的单调的巨声。因此列维纳斯说:「自由来自于知道自由受到了威胁。」[TI, 35]
也正是在恰恰是在我的愧疚中,自由上升为责任 [TI, 203]。我不再能自发地自由了,他者需要我为其需求作出回应。因此,无忧无虑的自由上升到为他者担负起责任。我的自由终于为「存在的重量」所正当化 [TI, 200]。
何谓责任?
责任具有四个特征:
应召性;
特殊性;
无限性;
非对称性。
责任的应召性意味着,承担起责任是在响应他者之脸的召唤:在他者的穷困面前,在寄居者、寡妇和孤儿面前 [TI, 77, 215],我感受到自己自由的不公。脸祈求和需要,因为需要而祈求,被剥夺了一切,而说「被剥夺」的前提恰恰是有权拥有一切 [TI, 75]——他者之脸转向了我,我是「被选中的」[TI, 245]。没有人能够替代我,我是不能回避的。我可以选择担起责任与否,但是脸转向我的事实意味着我已经是有责任的了,即使我拒绝承认自己有责任或拒绝担起责任。
责任是特殊的。从分离中已经预见到了责任的特殊性:因为个体的特殊性,每个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不一样。他者之脸显现时,对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相反,法律一视同仁地明确规定责任和某些行为的惩戒。这就让个体的责任与法律规定的责任不同。法律的责任是明确的,能够被「履行」的,比如我有责任纳税。但是特殊的责任要求的不是某种规定义务的完成或者某种行为的规避,而是我尽一切所能去回应他者之脸的需求。
责任是无限的。这里的「无限」与数学上的「无穷大」不同。它是说责任量是随着我承担的责任一起增加。不管做了多少,我仍然面临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无限的责任更是超越法律的,甚至是反直觉的:我的责任完成得越好,我的权利就越少;我越正义,就越愧疚 [TI, 244]。这与对善的渴望何其相似:「被渴望者不能满足渴望,反而加深了它。」[TI, 34]
责任是非对称的。第一重含义是,我拥有责任不是因为他者拥有同样的责任,不是因为我期待他者能够投桃报李。因为我不可能脱离自我去观察和描述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我能要求于自己的与我能要求与他者的完全不一致 [TI, 53]。因此,我不能要求他者和我有相同的责任。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责任不能够被条例化,它必然是超越法规的。

非对称性的第二重含义是,虽然脸表明了他者是脆弱而需要我的,但是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是他者拥有权威 [PL, 169]。他者比我更重要,而这是善的含义 [TI, 247]。脸在属于他者的高度召唤我从善;我承担起责任去回应和给予——而不是施舍——作为对高于我的存在的奉献 [TI, 75]。
就像列维纳斯青年时代就读过的,而后热衷于引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述的那样:
我们每一个人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是有罪的,而我是最大的罪人。
陀, 341
《卡》中有一个受自己良心折磨数年的杀人犯听闻,说道:
人们一旦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天国对于他们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现实了。
陀, 359
6 生死之间
死亡是列维纳斯和海德格尔的决斗。海德格尔写道,「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或成其本质。」[PLT, 222]自我的有限生命是否使形而上学者的渴望、对无限的责任的应答无效,甚至成为荒诞的偏执?毕竟,我生也有涯,而善也无涯。列维纳斯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无限的时间的话,善可以说是主观和疯狂 [TI, 280]。人在有限生命的前景面前,有何响应他者之脸召唤的义务,作答「我在此」(Me voici)?为何不 「为自己」而「成为自己」?毕竟「此在在每种情况下都是我的。」[BT, 68]
海德格尔的下半句话是,「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是因为其能够赴死。」[PLT, 222]

列维纳斯的成就在于,给了下半句原因,从而使上半句无效。人能够为他者赴死,则终有一死不再成其本质:
为不可见者而死,这就是形而上学。
TI, 35
不可见者等同于他者,因为他者之脸在言说,而不是被看见。
但这和脱离死亡有什么关系呢?试想为人父母的经验。生育 (fecundity) 让存在者能够拥有一种有别于自己之命运以外的命运 [TI, 282],把他者的可能性看作自己的可能性。我和孩子的关系是一种与他者的关系,我不能对孩子有完全的知识或者权力。不同的是,在这种关系中,我不仅是我,还是他者。我为这样的他者奉献时间,也就是生命;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为其而死。然而,我的死亡不过是无限时间中的短暂不连续,我的孩子也会有孩子。
作为存在论范畴的生育不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育 [TI, 247, 277]。也就是说,生育中的他者不一定是我的孩子。如果把他者看得比我重要,为其生、为其死,在奉献自我的过程中,每次对他者的直接回应都是在用无限的时间接力无限的责任。他者的无限性在召唤——无限的责任等着我的回应,无限的时间为我打开。若能应答来自他者的召唤,能够真正地把他者的可能性看作我的可能性,则我拥有无限的青春与生命,在非连续的时间中永生。
或许没有比这更好的譬喻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 12:24
生命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生而死。
7 后记:为了「神圣的神性」
他们常常说我做的是伦理学;但其实最终令我关切的不是伦理,或者说不仅仅是伦理。它是神圣,是神圣的神性 (the holiness of the holy)。
AEL, 4
为什么列维纳斯要这么费力地传达似乎已经存在的概念,利他?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列维纳斯关注的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和神学对利他的肯定来自于神谕 (divine command),且他认为整个圣经对自己伦理学的影响比犹太教大 [PL, 173]。但是,他是拒绝宗教和神学论证的:「不能还原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都还是原始形式的宗教」[TI, 79]。列维纳斯常借用宗教词汇,而其语境是他给宗教的定义——「不会堕为总体的同一与他者的纽带」[TI, 40]。下面这两句话即是他使用宗教词汇的典型:
人作为他者,从外朝我们来,是一张分离的—或者说神圣的—脸。
TI, 291
他者不是神的化身,但是正是通过他者非化身的脸,神的高度的启示被显现了。
TI, 79
这把我们带回了列维纳斯的核心概念「他者之脸」,以及为什么这和哲学上对于利他主义的论证截然不同。他的目标不是作为规范伦理 (normative ethics) 的一种流派的利他主义,而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相遇的现象学检验,证明确实有超出存在论总体的无限,让伦理的第一刻——他者之脸——成为一切伦理的基石,而伦理又会成为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石,就像我们在列维纳斯独特的语言哲学和时间哲学中看到的那样。

通常来说,哲学上对于利他主义的论证都要涉及到我们的能动性 (agency),而能动性来自理性或者自治性 (autonomy) 或两者的结合 [OHL, 9]。理性或者自治性 (autonomy) 这样的概念已经假设了总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有同样的理性或者自治性 (autonomy),它的思路是推己及人的:「因为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有理性 / 自治性……」在借理性之名的绝对律令中,立法者在假设自己拥有总体的审视者的地位,即上帝视角,但是立法者在这么做的时候仍然是总体的一部分,因其仍然在相信总体所假设的理性的地位。反之,在面对面的原初关系中产生的「汝勿杀」,不是依托理性,而是他者的超越性——伦理是先于存在论的;律令和责任的箭头从他者指向我,而不是由我自发——它和传统道德哲学的思路相反。
另一种由我自发的伦理是建立在同理心 (empathy) 上的:「因为我感同身受……」列维纳斯与这两种总体的思路恰恰相反:「不,我们不一样!」他指出他者与我的根本性不同是不可逾越的,即分离。我和他者是如此不同,乃至我必须借助「无限」来描述我对他者的体验。启示了无限的他者之脸,通过语言开启了我对自我享受的超越,对唯我的本真性的超越,对为自由而自由的超越。我担负起无限而非对称的责任,从而超越死亡。无限的概念是「想多于我所想」[TI, 62],无限的责任是行多于我所行,无限的时间是活多于我所活。
在大多数时间里我的生命对我是更亲近的,大多数时间人在照看他自己。但是,我们不能不仰慕神圣,……即,一个人在他的存在中,其更多的是委身于他人的存在而非自己的存在。我相信正是在这种神圣性中诞生了人。
PL, 172—173
8 后记之后
诚然,列维纳斯留给我们很多疑问。笔者举三例,不全面也不深入,邀请读者共同来探索:
1.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话语体系下进行对海德格尔的反叛是可能的吗?
这是德里达在《暴力与形而上学》中对《总体与无限》的发问,也促使了以言说和所说 (the saying and the said) 为核心概念的《异于存在或在本质之外》。《异》再次强调了我对他人责任之不可避:早在自我的「前史」中,我就是他人的人质和他人的替代了 [朱刚, 154]。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的故事了。
2. 列维纳斯的关于女性 (the feminine) 和爱欲与生育的讨论是否是大男子主义的?
上文中没有涉及到列维纳斯在栖居和爱欲讨论中涉及的女性,和她们的沉默与温顺。Tina Chanter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在两种读法中探索了列维纳斯的性别政治与伦理的关系 [Sean, 114-115]。
3. 列维纳斯是西方中心的吗?
《总体与无限》中对「东方智慧」的提及是为了表示自己与它的不同 [TI, 218]。列维纳斯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现出西方中心(甚至种族歧视)倾向:「人类由圣经和希腊人构成……其他的人类都是舞蹈。」Robert Bernasconi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研究 [Crithley, 176]。
对于一个思想家进行批判性解读带来的持久对话,不仅是对他的质疑和更深入的理解,还是我们对自己的当时当地反思的切入点,乃至行动的开始。所谓的第三波列维纳斯研究潮(前两波分别是文本解读和把他置于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目的在于把列维纳斯的思想置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学界「激进化」列维纳斯的探索,涉及领域很广:动物解放、环境问题、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等 [A&C, xi]。这是极其可喜的现象。或是列维纳斯本人的政治局限性在逐渐被后来者突破,或是列维纳斯的「伦理先行,政治随后」的「随后」正在发生——不管是哪种情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第三波列维纳斯研究潮都例证了列维纳斯思想持续的活力和相关性。他者之脸不断在言说,很多个「我」不断在响应。/

列维纳斯作品:
[TI] Lévinas, Emmanuel., and Alphonso Lingi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Pittsburgh: Duquesne UP, 2007.
[DF] Lévinas, Emmanuel., and Seán. Hand. Difficult Freedom : Essays on Judaism. London: Athlone, 1990.
[PL] ‘The Paradox of Morality: An Interview with Emmanuel Levinas,’ trans. A. Benjamin and T. Wright, in R. Bernasconi and D. Wood (eds) 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 Rethinking the Oth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68–80.
参考书籍:
Atterton, P., & Calarco, M. (2010). Radicalizing Levinas. Albany, N.Y.: SUNY Press.
[CCL] Critchley, Simon, and Bernasconi, Rober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vinas. Cambridge UP, 2002.
Davis, Colin. Levinas : An Introduction (1996).
Hand, Seán. Emmanuel Levinas (2009).
[OHL] Morgan, Michael 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vinas. New York, 2019.
Large, William.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2015).
朱刚,《多元与无端: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
Critchley, Simon. "Five Problems in Levinas’s View of Politics and the Sketch of a Solution to Them." Political Theory 32.2 (2004): 172-85.
其他:
[AEL] Derrida, Jacques. Adieu to Emmanuel Levin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P, 1999.
[BT] Heidegger, Martin,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S. Robinson. Being and Time (1962).
[PLT] Heidegger, Martin, and Albert Hofstadt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 London: Perennial Library, 1975.
[PWD] Descartes, René,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and Dugald. Murdoch.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1984).
[陀] 陀思妥耶夫斯基,荣如德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