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機女孩”和“簡單男孩”談起|圍爐·FDU

在《圍爐夜話:一顆腎背後的道德、創作與身份爭議》中,我們探討了性別對於敘事的影響,兩名女作家的紛爭往往被塑造成“女人扯頭花”的八卦,回歸到“mean girls”“女人就是事多”的刻板印象。 英文脉络中的“mean girls”最初由學者提出,旨在概括青春期女孩對彼此施加的隱性攻擊(如白眼、造謠、忽視對方),卻在近些年被大寫特寫、成為對於女孩的刻板印象。 中文脉络下的“心機女”既用於描繪那些表裡不一、善於勾引男人、陷害朋友的女性,又用於單一化女性的行為動機——“女人就是事多”。 與之相對,男性總被認為是大大咧咧、毫無心機的“簡單男孩”,他們之間的友誼也囙此是絕不塑膠的“兄弟情”。 本期夜話則從五名圍爐成員的自身經歷出發,探討“心機女孩”“簡單男孩”式刻板印象。 椰子和善長反思了自己作為曾經的mean girl和霸淩旁觀者的經歷,螽斯分享了大學裏與“mean girls”截然相反的女孩們的友情,吉豆回溯了自己被“歧視”的遭遇,點明男孩的刻薄與諷刺同樣存在並造成傷害, 金魚則分析了“心機女孩”“簡單男孩”標籤背後的迷思與系統性問題。

椰子|我從小就是一個符合主流要求的成績好、長相“正常”的女孩,並沒有遭遇過霸淩,但也恰恰是這種“好孩子”特質把我架在了便於拉攏小團體、發動隱性攻擊的位置。 小學時,面對不喜歡的女生(而對方又很喜歡我),我並不會直接表達我對她的態度,而是通過生日聚會不邀請她、特地不選擇她做我的同桌等等行為來間接傷害她。 那時可能覺得,自己在老師和家長眼中都是乖女孩,對方也是班級裏受歡迎的女生,如果直接和她鬧掰,我就不再能扮演乖女孩,也不再受歡迎了。 而那時不喜歡對方也是出於一種有毒的厭女思維——我總是用“婊”來揣測女生,總覺得她表現出的某種特質肯定是為了吸引男生注意。 “心機婊”“綠茶婊”“漢子婊”……社會文化生造出許多“婊”來歸類對女人的辱駡,尤其是辱駡她明裡暗裡“勾引”男人。 我浸淫在毒藥中,竟也不自知地生產了毒藥。 唉,現在想來真是羞愧! 正如陳亞亞所說,婚戀領域之所以對女性顯得格外重要,不恰恰是性別壓迫的結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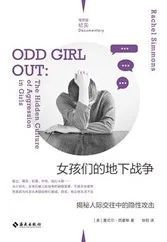
小學時我也真誠地認為“和女生玩真複雜,男生真簡單”。 現在想想,這多半是偶像劇的荼毒。 偶像劇裏總有個“心機女二”,發動各種“隱性攻擊”,妄圖奪走男主對於女主的愛; 而裡面的男生多半癡情貼心,十分“簡單”。 回到現實生活,一些女生可能“心機”,也可能不“心機”,但那時的我總是傾向於她是“心機”的,從而確證我對於“心機女孩”的刻板印象,如此一直迴圈。 但這種想法到了一個女生少的地方就會自動破除。 初中時我被選入了男女比懸殊的(男女比為何懸殊又是另一個性別議題了)競賽班,我成為了一個成績一般的女生,妥妥的弱勢群體。 我在當時有很明顯的被凝視的感覺,父權的大象清晰可見。 (比如,一群男生在班裡大聲講黃段子,有時還代入幾個女同學的名字)甚至,我反而要感謝競賽班的“有毒”環境讓我有了性別意識。
成績和性別以及它們的疊加在霸淩中扮演的角色值得一探。 我曾經圍觀並參與了競賽班所有人對於普通班兩個女生A和B的霸淩。 如上所述,競賽班是一個典型的boy's club。 男生們覺得A長得醜,B胸大且暴力(事實上他們也只是眼熟A和B而已,並不認識A和B),於是當他們想辱駡(“調侃”)其他男生時就會說“你愛A!” “你愛B!”, 幾個女生就旁觀著,有時也“調侃”幾句。 我媽當時也知道我們在“調侃”B。 她跟我說這麼做不對,萬一B後面名聲被我們搞臭呢。 我說沒關係,因為B只是個符號,大家只是想發洩。—— 但現在想想,恰恰是因為只把她當作符號,我們在“調侃”的時候才不會顧及她作為一個人的感受啊!
我總想,如果當時有人教給我真正的平等觀——“你們‘調侃’她們的行為本身就是錯的,因為你們沒有把她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我是否會停止旁觀、制止霸淩。 但讓我感到無力的是,作為一個成績一般,也囙此更沒有話語權的女生,我的制止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當然,如果我是一個男生可能又會遇到其他困境,比如因為制止霸淩而反過來被男性群體霸淩。) 讓我感到無力的還有,在一個本身就彰顯著不平等的競賽班,學生們已經因為成績優异而享受到了特權(更好的師資),又如何能信服“你們沒有把她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的合理性呢?
談談轉變。 上大學後讀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不禁深思我們的社會文化所刻畫的女性情誼——不是拉小團體就是“毒閨蜜”。 若要從“心機女孩/mean girls”向“我的天才女友”轉變,我認為關鍵在於認識人的複雜性、關係的複雜性。 不因為關係重要而用以威脅“不這麼做我們就絕交”,也不因為關係重要就進行暗地裡的攻擊,而是因為關係的重要而更勇敢地去面對問題。 而如果我們的腦海中仍然不可抑制地蹦出“心機”“婊”等詞語,我們可以在“原諒”自己的同時深刻反思。 “厭女”的心態雖難以消除,卻可以成為對“女權”概念理解轉變的開始。 正如上野千鶴子所說, “人在成為女人的時候,要先將‘女人’這個範疇所背負的歷史性的厭女症姑且接受下來。如果滿足於這個範疇所指定的位置,那麼,‘女人’就誕生了。可是,女性主義者,就是對那個指定比特置感到不滿、對厭女症不能適應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從厭女症出發 的女性主義者。 做一個女性主義者,就意味著與厭女症的糾葛和抗爭”。

吉豆|因為我所在地區的教育水准較為落後,我小學時曾多次轉學以期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 在所讀的三個小學中我都曾因為不同的原因受到過一定程度的“霸淩”。 在這裡我給霸淩一詞加上了引號,因為在受到一定的身體傷害和心理壓力的同時,我也能够理解對方對我情緒與歧視的來源。 “霸淩”對於我來說似乎是環境下的客觀產物與必要的承擔結果。
我曾受欺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成績優秀。 因為轉學後會擠掉原來第一名的位置,所以很容易引起別人的不滿。 比較嚴重的一次是我在上四年級的時候,原來的第一名因為考試沒有發揮正常而在教室外哭泣。 我當時於心不忍,走去安慰他,沒想到他或許是惱羞成怒,竟然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 我又痛又震驚。 向老師反映,但她卻只是安慰了我幾句。 白衣服上的鞋印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裏,但當時的情緒早已隨時間的洗刷而淡然了。 對我來說,此類經歷並未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因為我仍然可以通過和別人的相處來為自己正名,贏得大多數人的友誼。
但是後來遇到的另一種“歧視”,更深地貫穿了我的所有生活。 這裡的歧視我也打了引號,因為我覺得這似乎依然是我自己引起的客觀後果。 因為下頜發育過度,我的臉型從側面看起來和“正常人”有所區別,我的不自信不斷增長,青春期發育的女性很快感受到男性的凝視,男孩子們會開始討論誰的胸大誰的胸小,誰黑誰白,我的下巴也難避免會成為話題。
上述的兩種“霸淩”,我自己心裡都很難認為是真的非常惡意的霸淩。 在前一種情况中,因為成績好而受到嫉妒與憎惡,這樣的短暫性偏見終究是能够通過與同學們的相處與發展而改善的,在這種“霸淩”中,我也深知自己並沒有主觀的惡意與錯誤; 而在後一種“霸淩”中,針對先天特徵的嘲笑與諷刺,卻是我非常難以改變與扭轉的。
在青少年發育與成長的過程中,同齡男性對於女性生理與外貌特徵的點評貫穿其中(並非女性沒有相應對男性的點評,但僅以個人的觀察而言,男性更勇於在公共場合中談論與傳播)。 而在這個階段的教育中,對於美和醜的定義往往是確定和單一的。 就像瑪麗·道格拉斯談到的清潔與污穢的文化構造性一樣,青少年所接觸的環境與教育中,對脫離簡單秩序與架構的事物及其特徵並沒有足够的包容。 於是,黑皮膚、肥胖、畸形的是必然難以與美聯系的,這類女孩也往往成為男孩調侃嘲笑的對象。
在我當時的境遇中,儘管我能通過學習與交流和同學們形成良好友愛的關係,但當我作為一個“女孩”被男生點評的時候,我仍然難以逃脫這些讓自卑深植我心中的議論。 當男生們在黑板上玩你畫我猜,畫出一個長長下巴的我時,那種受到羞辱的感覺始終强烈。 我認為對於男性來說,其中部分人在後來的學習與生活中會經歷一個自我再教育的過程,逐漸變得更加開放與包容,而部分男性可能會繼續維持他們的“自信”與刻板觀念。 (女生也何嘗不是這樣。) 但無論他們怎樣變化,曾經被傷害和刺痛的我依然不斷想要填補一直存在著的內在的自卑。 我知道悅納自己的道理,但是這個不斷重建自信的過程我自己並沒有信心。
所以在我看來,mean girls和simple boy既是一種不完全真實的描述——男孩的刻薄與諷刺同樣會造成傷害,並且不論男女,他們可能都是該階段性文化環境與教育引導下的暫時性產物,帶著對世界與生活單一片面的認知。 或許今後教育的根源性改善是值得期待的,我期待著進一步對多樣性的包容和對女性關於男性凝視的解放。

善長|和椰子一樣,我也沒有遭遇過霸淩,而且坦誠說應該屬於在社交中有“優勢地位”的那一類群體,和大部分班上的同學都相處得來,還與兩三個最要好的朋友形成某種“鐵X角”關係, 和女生關係也算融洽(就像楊紅櫻小說裡面描寫的那種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 我記憶裏很少有像椰子這樣真實而具體的女生之間或針對女生的“霸淩”故事,甚至連旁觀的經歷也幾乎沒有,囙此基本上無從談起。 但我記得從小學高年級起,男生間就有了所謂的“幫派”,存在“霸淩”。 初中時在一個比較亂的學校,霸淩現象就變本加厲。 那時班上有兩三個比較沉默內向的男生,我知道他們會給那些已經在“混社會”的男生錢。 有一次下課我見到當時一個“幫派”的“小頭目”男生A問男生B要錢,我當時去制止,A倒是不打算要了,但後來問B,知道B還是給了A,因為怕之後被報復。 我當時不屬於被“霸淩”的人,甚至在班上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在一些當面發生的“霸淩”事件中起到一點作用,也基本不會囙此被報復。 但我所能做的仍然很有限,且當我游離於那個“霸淩者”的圈子周圍時,介入的程度也必然很微弱,這看似悖論卻是現實。 “小頭目”之上有“大頭目”,教室之外有廁所、有回家的小路,他們總能找到別的管道繞開你這個輕微的“麻煩”,讓“井水”最終不犯“河水”。
此外,某種意義上更無奈的是,在一部分情况中,我恰恰和那些“霸淩者”同學更相處得來。 而即便在霸淩事件中我會出於樸素正義和同情幫被霸淩的同學說話,但那之後,我們常常並不會真正成為朋友。 比如上面事件裏的A和B,A和我經常在體育課上打籃球,儘管不是好朋友,但也算是熟悉。 但B平時不參與活動,也不好相處(這有時更會成為他們被霸淩的理由),我確實不會和他成為朋友。 個性與霸淩事件有時互為因果。 在一部分情况中,就存在這樣的迴圈。
這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 所有經歷和環境都會造就一個人的個性,“霸淩”誠然是惡,但其中的“結構性問題”同樣不可忽視。 在現實中遇到一個令我厭惡的人時,我逐漸學習更多地考慮他的過往,和曾經遭遇的“惡”,而不是依據眼前種種下判斷。 但這有時也會碰到限度,因為令人厭惡的言行就是現實遭遇的情况,而包容不快和厭惡帶來的自我損耗也是真實的。 到什麼地步善良才不會變成過度的濫情? “過去”的解釋力有多大,隨之應該賦予的體諒的限度究竟在哪裡? 在決定論和個人能動性之間存在一個尺度,這個尺度可能是模糊的,令人在具體的情境中常常會變得困惑。 我只能時刻讓自己意識到我此刻的存在同時背負著過往,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幸運,同時避免被不幸捆綁。 而同樣他人此刻的存在也背負著所有的過往。

螽斯|最近我看到一比特學長在豆瓣上評論《甄嬛傳》的時候提到成年女性聚在一起會自然有一種勾心鬥角的氛圍,我不是很同意,尤其因為身邊的朋友們組建了“甄嬛傳學術小組”,我覺得大家非常可愛,所以忍不住單方面叭叭叭了起來。 我感覺上大學之後我完全沒有感受到一絲一毫的女性之間的“勾心鬥角”,我看到玩梗、表情包等構成的社交内容很强的文化,也看到女性朋友一起出遊、互相拍美好的照片、真誠分享、坦誠地相互傾訴相互支持, 我還看到女性朋友(有時候包括我自己)以直截了當具有一定攻擊性的管道公開起衝突或者解决衝突。 這些與“心機女孩”完全不同的氛圍,一方面源於女同學們自身的成熟和進步,另一方面我猜也和鬆散自由可以自主尋找夥伴的氛圍有關,有更合得來的人和氣場不太合的人、有玩得好的時候和起小衝突的時候,這些都很正常, 在人際關係自由流動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過調試人際關係距離來解决(按這一猜想,在寢室關係當中,難以避免的摩擦和似綁定般的親近之間的衝突,或許會導致隱形的孤立或角力更容易存在。另外,我上大學後發現男性在不能明面上撕破臉的綁定的“共同體” 中似乎也會有所謂“心機”的行為。) 我比較關注的問題是當女同學以嚴苛的“是非”標準公開譴責甚至攻擊他人(尤其是在性別等議題上),即便有時占理,也顯得很“法利賽人”氣(即教條地遵循和看待“是非”標準)。 當然,男性如果有相似的行為,也很可能招人厭惡。 不過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對公開批評甚至攻擊他人,尤其是女性公開批評他人的行為多一點包容,至少公開批評他人的人有直言不諱的勇氣,這是和那種暗地裡中傷別人的行為截然不同的。

金魚|“心機女孩”和“簡單男孩”的標籤一方面反映了我們潛意識裏對關係的價值取向:關係應該是簡單的。 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簡單”的關係真的就是更好的關係嗎? 或者說,關係真的是簡單的嗎? 售貨員和顧客的關係很簡單,但顯然我們並不滿足於只擁有這樣的人際關係。
Ellen Goodman在The Tapestry of Friendship裏將女性之間的情誼和男性之間的情誼(根據刻板印象)分別描述為friends和buddies。 Buddies之間的關係往往很簡單,通過共同活動(運動、比賽、事業等)相互聯系並且相互認同(彼此的男性氣質),是一種”you are OK,I’m OK”的關係。 雙方可以有很長時間的關係、可以共同面對困難,但卻不可以向彼此袒露脆弱的一面。 Friends之間的關係則相反,她們並不通過相互認同確認關係,而是相互接受——也就是說她們不僅見證了彼此光鮮的一面,也擁抱了彼此脆弱的一面。 在文章最後Goodman也指出,這種“女性版本”的友誼已經逐漸成為了公認的理想中的友誼。 在這個破除偏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由於人都有脆弱的一面,關係也應當是多面的、能够承載這種複雜性的。
然而即便我們現在已經很容易接受關係的複雜性在於承載脆弱這一點,我們顯然還不敢承認關係的複雜性也在於我們並不是全然沒有私心的聖人,並且由於人類社會化的特點,我們並不總是會像野獸一樣表達出我們的攻擊性。 女孩們的“心機”在於暗戳戳地為自己謀劃,男孩們的“簡單”在於心胸坦蕩毫不計較; 然而成年人的社會真的是這樣的嗎? 實際上這樣對立的幻想往往只會加諸少年或是兒童身上。 女孩們被認為是更早熟的,囙此我們在她們身上投射了對社會化的成年人之間的關係模式的失望和厭惡,而男孩則被幻想成是免於“污染”的。
另一方面貼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的標籤也來源於社會對性別分工的期待。 女性被認為是應該善於處理感情和關係的,而情感在社會生產、工具理性的邏輯裏被認為是冗餘,是只存在於私域、不值得也不應當被拿到公域來言說的東西。 當社會把情感勞動理所當然地丟給女性的時候(例如教育女孩子要細心、為他人著想),也認為情感勞動是低級的勞動,囙此女性再怎麼善於處理關係都只是“心機”而已——不僅是多餘的、沒用的,也是上不了檯面的。
雖然我們覺得情感、關係問題是上不了檯面的問題,但顯然我們處理這些“小問題”的管道卻很糟糕。 雖然學校是兒童成長中最重要的學習如何與人相處的地方,但學校卻很少提供情感教育,特別是應試教育體系裏的學校。 一方面成年人期待著少年兒童是純真無瑕的,另一方面又拿工具理性的邏輯治理學校,認為和成績相比人際關係只是過家家。 但如同成年人的社會無法真的像機器一般運作,孩子之間被權力塑造的關係也無法被排除在只看見成績的系統之外。 校園霸淩中有許多惡意傷害需要被更嚴肅地處理,也有許多傷害是可以通過情感教育來避免的。
文|椰子 吉豆 善長 螽斯 金鱼
圖|來自網絡
審稿|黃彥中
微信編輯|張宇軒
matters編輯| Marks
圍爐(ID:weilu_flame)

文中圖片未經同意,請勿用作其他用途
歡迎您在文章下方評論,與圍爐團隊和其他讀者交流討論
欲瞭解圍爐、閱讀更多文章,請關注本公眾號並在公眾號頁面點擊相應選單欄目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