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人(二)——在疲憊的深夜等待不可知的春天|圍爐·CUHK
疫中人(二)——在疲憊的深夜等待不可知的春天|圍爐·CUHK ——


兩年前的春天,各地的疫情逐漸趨於平緩,生活的秩序開始慢慢恢復正常,而在上海,今年的春天卻並未如期而至。
疫情之下,隨時準備進入緊急動員抗疫模式的“戰時狀態”取代了原本生活平穩的常態,秩序隨著政策的變化和疫情的波動永遠處在不確定裏。 突然大規模爆發的疫情讓許多基層組織單位措手不及。 位於浦東新區的一個社區裏,居委會意外在疫情爆發之初就被集體隔離,幾名志願者在封閉的樓棟中實驗了一場社群自治。

1
“穿著雨衣的臨時志願者”
我3月份的時候在學校,最開始疫情還沒大規模爆發時,疫情軌跡就很多次涉及了我們學校,所以學校從3月2日左右就已經開始封校了。 那時候我們在學校裏大約關到了3月23日左右,這時候外面感染的人已經逐漸多起來了。 學校讓有上海居住地的學生先回家,然後我就回了社區,沒想到剛回家兩三天,社區裏的感染者就逐漸多了起來。
3月24日那天浦東新區全員核酸,我就報名了臨時志願者。 那時候我們的防護裝備非常簡陋,連防護服都沒有,穿了件雨衣,戴上n95口罩和手套就去做志願者了。 結果當天核酸結果一出發現我們樓裏就有陽性,那天開始我們樓就被封了起來。 當時居委會還是正常地來組織大家做核酸的,結果由於一個志願者感染了但他自己不知情,於是在和居委近距離接觸聊天的過程中感染了居委會的社工,而其他居委會人員也囙此成為了密接。 所以居委從我們社區開始出現疫情的第一天就被集體隔離,鎖在辦公室裏,這就直接導致初期的管理很混亂。 後面街道還派了10名志願者來,結果他們由於跟居委會是次密接所以剛一過來就被隔離了。 在核酸轉陰並解除隔離之後,他們又說不做了。 因為他們覺得住宿環境太差,每天幹活也挺多,所以就直接捲舖蓋走人了,一點忙都沒幫上。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街道,甚至可以說整個浦東新區都蠻混亂的。
我們被封在了樓裏,居委會又被封鎖在辦公室,管理很混亂的情况下,我們樓的居民就只能自發組織起了志願者的工作。 最初是我認識的一個鄰居主動站出來說,既然都出來當志願者了,就一直幹下去吧。 其實說不幹也很簡單,沒有人會指責我們,只是覺得總要有人站出來為大家安排好這些事情,不能讓局面就這麼混亂下去。 我就覺得不能讓他一個人承擔這麼多,居民的核酸檢測,物資運送,這麼大的工作量不能都堆在他一個人身上,於是我也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我們樓棟的志願者。 最開始只有四名志願者在維持所有疫情期間樓裏的工作,沒有人告訴我們要做什麼,應該怎麼做,也沒有人給我們提供物資和設備的幫助,所以只能我們自發組織志願者,安排各種大小防疫事宜。 就這樣,社區進入了一種樓棟自治的狀態。
2
“疫情中的守望”
剛開始的工作還蠻艱難的,畢竟真的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那時居委會每天給一棟樓發兩套防護服,意味著每天一共只有兩個志願者參與輪班,可這樣一個志願者得連續高强度工作六小時,囙此一天兩套防護服肯定是不够的。 所幸我們樓裏有一戶人家是醫生,他捐了一些手術用的衣服,相當於簡單的防護,總歸比雨衣好一些。 後來到了四月初才每天能發到四套防護服,偶爾會多發兩套。 而具體的志願者工作方面,搬運物資倒還好,只需要按照名單把樓下的物資分發到對應的家庭就可以,只是跑上跑下累了些,但這些體力勞動算得上是疫情期間最簡單的工作了。
比較麻煩的是做核酸和發抗原檢測盒,記得我們第一次組織安排大家做核酸是28號的時候,當時大概是晚上七八點了,天也挺黑的,那次是浙江的醫生來幫我們做核酸。 一開始他們是把我們所有人全部一起叫下來,而我們有十八層樓,只有兩個電梯,如果散著下來一批批等電梯會耗費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們就催大家快點都出門準備下樓。 結果下來後發現做核酸有各種意外的突發事件,一會是熱敏紙沒了,一會是咽拭子的棉簽沒了,不斷地因為這種事件中斷核酸檢測行程,這些完全在我們意料之外。 囙此等待做核酸的隊伍就排的很長很長,效率非常低下。
第二次核酸的時候我們就跟醫生商量,能不能等志願者把所有準備工作做好後再上門做核酸。 我們四個人開了個會分配任務,提前一天晚上挨家挨戶敲門,提醒大家截圖好健康雲的核酸檢測二維碼,幫不會操作手機的老人也登記好資訊,準備好備用的檢測用品,沒了就換。 改變了一下策略後,檢測就快了很多。

我們樓裏其實老年人是比較多的,他們在疫情期間遇到了蠻大的困難。 比如他們不會用手機訂菜,不會截圖做核酸提前要準備的二維碼,坐在輪椅上不方便拿抗原拿物資,我們就要上門幫他們逐個解决這些問題; 確診了陽性但尚未被轉走的人也有許多,我們要幫他們上門送物資,清理垃圾; 還有一些需要藥的病人,這是很緊急的需求,我們當然要想辦法盡可能幫到他們。 一來二去的就跟樓裏的大家都熟悉了起來,他們遇到困難就直接來找我們幫忙解决。 我在此之前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大部分鄰居,見過的也僅僅只是有些眼熟,這次志願者的經歷讓我一下子和很多人有了交流,也感受到了這棟樓的溫度。 我們樓上有個獨居的陽性感染者,周圍的鄰里也會時常關心他,送去一些自己也並不充裕的牛奶雞蛋。 疫情下的鄰里關係似乎尤其和睦親密,大家都在互相守望著期盼熬過這段時間。
樓裏還有一家住了兩個人,一個人精神不太正常,另一個是八十幾歲的老年人,兩天從床上摔下來了兩三次,兩個人都不能自理生活,在疫情下也就尤其困難。 一天我們穿著防護服去辦他們測抗原的時候,發現那個老人躺在地上,卡在床和窗戶的夾縫裏,他身上的衣服亂糟糟的,神智也有些不清晰,聽不清我們在跟他說什麼,可能已經在地上躺了一兩個小時了。 我們擔心二次傷害便不敢隨意動他,就直接聯系了居委會打急救電話,但他被救護車接走後,醫院說他沒有生命危險,特殊情况下不能接收這樣的病人住院,他就被原路送了回來。
幾天前我們收到了一條消息,說那位老人已經去世了。
3
“只能親眼看到的資訊”
不過最影響我們工作的是疫情期間的資訊差,我們和居委會以及居民的直接聯系是比較通暢的,但是很多時候居委會接收到的內容也是模糊不清的,街道或者更上級有時就沒有給他們傳達明確的資訊。 比如有幾次疾控中心來複測,這就說明前一天的核酸混檢有陽性,但是問街道和居委會這些資訊的時候,他們說沒有收到這方面的通知。
還有一次疾控通知居委會說某家感染者已經被轉運離開了社區,但實際上他還在樓裏,也沒有人通知我們他還沒走。 我們發現這件事還是在有一天發物資的時候,他們問我們能不能下樓去拿。 像這樣的事經常發生,很多事情追溯不到一個可靠的資訊源頭,只能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也只能通過親眼去看來得到許多消息。
我們居委書記寫的辭職信,《春天快來了》,說沒有人通知他們什麼時候來做核酸複測,沒有人通報社區居民的感染情况怎麼樣,也不知道健康雲顯示的核酸報告是否可信。 這封信講的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事實就是我們只能通過自己看到的情况來判斷真實的數據。 食物、藥物、防疫用品的短缺,混亂的資訊,死板的命令,遙遙無期的解封日期,我們不知道我們生活在何種當下,也不知道等待著怎樣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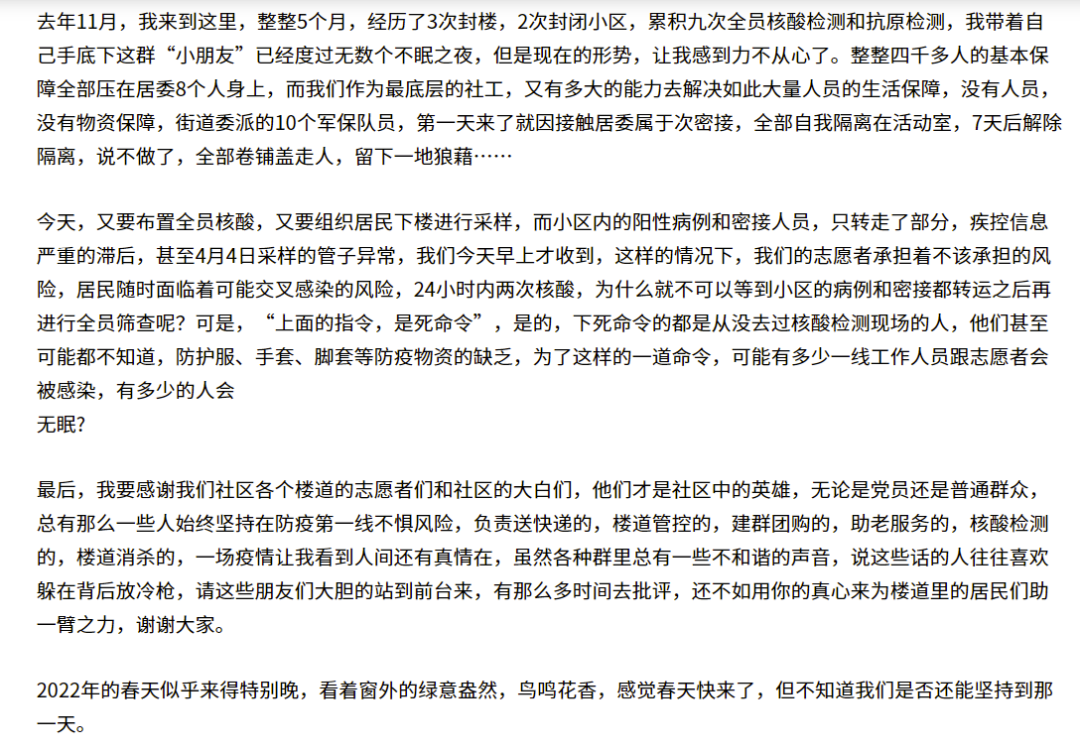
就這樣我們四個志願者輪班,負責搬物資、幫忙做核酸、給居民發通知溝通資訊、消毒樓棟大廳和電梯、幫不會自測抗原的人上門檢測,什麼需要幹,我們就得頂上什麼崗位,每個人每天連著工作三個小時,一天天重複著輪下來。
4
“等待不可知的春天”
其實起初來報名當志願者,根本沒有考慮太多感染風險的事情,當時我們社區還沒有感染者,只是沒想到第一天就測出了好多陽性。 不過後來逐漸發現自己需要暴露在更危險的環境裏,比如要去處理感染者的垃圾等,漸漸意識到了風險,也沒有考慮放弃當志願者。 畢竟志願者一共就那麼三四個人,一直順著慣性就做了十幾天,覺得做好防護措施也沒什麼。

剛開始穿上防護服那天覺得勁道很足,畢竟是很陌生的體驗,覺得自己好像真正成為了一名正式的志願者大白,那是我之前會覺得有些許距離感的身份,在這種新鮮感和使命感的驅使下也沒覺得工作有多累。 後面有三小時一次的輪班,身體上的疲勞也是可以應付的,比起門口可能需要早六晚十連軸轉,騎著電瓶車運物資的志願者,我們的工作還是輕鬆不少的。 但我們逐漸發現作為疫情下的志願者,需要應對很複雜也很多變的環境。 這是我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碰到疫情,許多方案都需要不斷地調整優化,如果一直按照一套死板僵硬的規則操作會很大程度降低效率,政策的改變也時刻影響著我們的工作內容。
記得健康雲系統換成核酸碼的那天,我正好輪到了最晚的一班,理論上應該是從五點半到八點半,但突然在下午臨時通知社區要做核酸,而整個社區26棟樓一共只有三組醫生來了。 我們本以為到了晚上八九點就可以暫時不做了,沒想到街道通知我們今天無論如何都要做完,所以我就一直等到了晚上十點才終於等來了醫生。 當時防護服的數量很緊缺,由於防護服每天都要換洗,為了節省防護服,那天晚上就沒有人和我換班,我只能自己一直等下去,一直到了12點一刻核酸檢測才終於結束了。 七個小時後我終於第一次脫下了防護服,喝到了水。 這天已經是我作為志願者連軸轉式工作的第13天了。 深夜十點半,從一歲小孩到七八十歲老人,全樓三百多比特居民都被從家裡叫到樓下做核酸。 鄰居們抱怨著為什麼要這麼晚下樓,周身紛亂的聲音在耳邊不斷地縈繞著,可我們根本無能為力,上面給的命令就只能實行,我們能做的只有優化流程,儘量減少耽誤大家的時間。 做核酸的醫生連續高密度工作,累得半死不活,居委會也近乎癱瘓,所有人都疲憊不堪。 那個夜裡,一種巨大的荒謬感籠罩著我。 今年的春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呢,我不知道,也看不到。
文| Vinyl
圖|由受訪人提供
審稿|何亦陽
微信編輯| Tho
matters編輯| Gigi
圍爐(ID:weilu_flame)

文中圖片未經同意,請勿用作其他用途
歡迎您在文章下方評論,與圍爐團隊和其他讀者交流討論
欲瞭解圍爐、閱讀更多文章,請關注本公眾號並在公眾號頁面點擊相應選單欄目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