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 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形成与特征|洪朝辉
野兽按:此次转载的三篇文章来自程晓农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一期,洪朝辉在“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形成与特征”一文中,用3C文化(儒家、中共和权力资本文化)这一组概念,解析了改革以来形成的权力资本文化与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渊源及共存关系。改革中政治权力不断扩张,资本的地位有所提升,权力和资本的结盟虽然巩固了政权,却养育了制度性腐败,遏制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摧毁了道德,权力和资本在没有政治权利的社会大众面前表现出极度的傲慢;官员和富人的权力越大,弱者和贫者的权利便越小,由此孕育着难以消解的社会冲突。
在“党国困境与可能的出路”一文中,作者北山指出了目前这种困境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古洪能的“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与前景”一文则从社会变革力量与反变革力量的博弈分析了中国走出现存政治困境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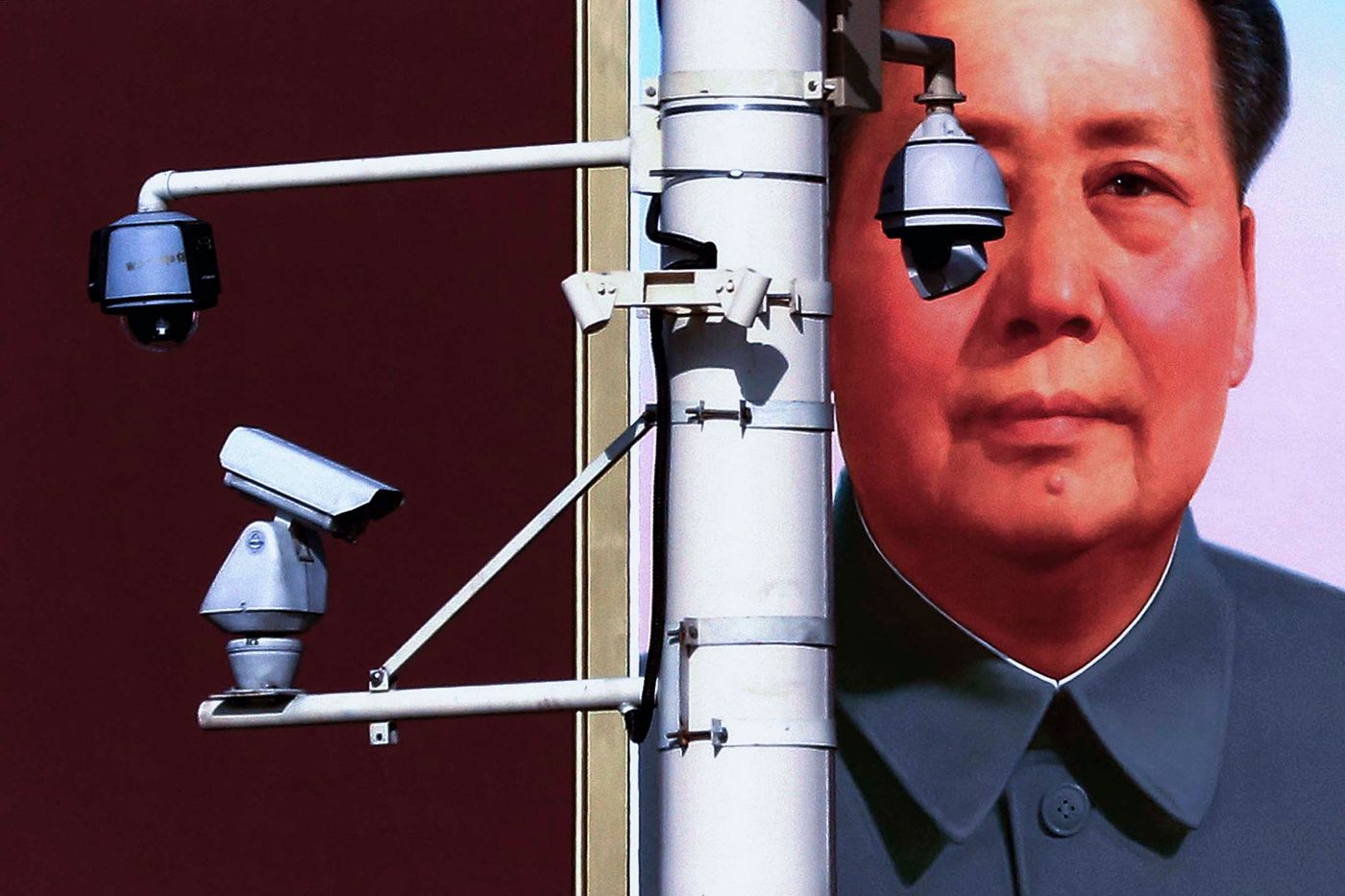
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形成与特征
洪朝辉
一、 导论
二、西方公民文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区别
三、权力资本文化的特征: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利的同步增长
四、权力资本文化的特征之二:社会参与的有限性
五、权力资本文化的特征之三:社会政治宽容的选择性
六、结论
【注释】
一、 导论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权力资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它与以往中国政治文化的两大传统,即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和中国共产党文化(Communist Culture),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三个基本要素,简称为3C文化。研究3C文化杂交和复合的过程及其特点,对于理解目前和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先以西方的公民文化为参照,探索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共同特征;然后分析在公民文化、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共同催化下,中国的权力资本文化经过30年(1978-2008)的孕育所形成的一些初期特征;接着讨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本文化究竟是中国政治文化历史演变的一个短暂插曲,还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固有特性的一个可能的长期存在?最后,本文还将分析权力资本文化对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自从Garbriel Almond在1956年第一次对政治文化给出定义以来[1],出现了众多的学派与解释,笔者将其归纳为三大主要学派:其一,以Almond和Verba为首的“政治态度与取向”学派,主张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的一种态度、取向、知识、心理和信仰,因此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取向和感情偏好,而不是客观的行为方式,但它们又是政治行动与体制建构的基础。[2]其二是以Lowell Dittmer为代表的政治符号和沟通学派,强调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这种符号达到互相沟通的目的,所以政治文化是代表一个团体或民族的政治符号,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态度与感情;方法论上,政治文化是可以通过实证和问卷等手段进行客观检验的。[3]其三是以Wildavsky为代表的政治理性学派,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感情,因为政治文化是社会内生的,植根于本民族、本国的历史与结构,而不是外来的政治偏好。[4] 50多年来,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演变方向是由宏观到微观、由宽泛到狭小、[5]由主观意识到理性行为、由难以测量的个体取向到可以观察分析的民族行为,为政治文化的可定量、可预测、可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6]
将上述西方政治学的定义运用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界定中国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和内涵;在此基础上,找出要素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联系与区别;最后,可以通过观察一些具体事例,分析这些要素对中国现实政治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对可能出现的中国公民社会、民主体制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反作用。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判断中国的政治文化究竟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一种交流的符号、一种理性的行为,还是三者皆而有之或混而合之?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大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由一种强势的政治文化主导社会。然而,经历30年改革之后的当代中国,其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一种文化要素能主导各个领域。1949年前的两千多年历史当中,儒家文化基本上主导了中国;1949年到1978年期间,儒家文化在政治运动的强烈摧残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它以强权为推行手段统治了中国30年;但在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间,随着共产党全能政治的削弱、传统国学和民族主义的复兴、西方公民文化的引入,尤其是权力资本经济[7]的盛行,新的权力资本文化开始成型,并导致中国政治文化中新旧要素并立同存、相互制衡、相互影响。这样的政治文化既有新的特色,又包含了旧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将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必须指出,从历时性结构角度去看,过去6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在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层面出现了从儒家文化、中共文化到权力资本文化的变迁,并向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提出了挑战,因为3C文化差别显著,难以兼容;但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结构而言,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宏观体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因为3C文化其实分享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代际交替和互动消长在中观政治(mesopolitics)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可以预见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3C文化的并存更多地意味着新旧政治文化的重叠和混合,由此形成了一股合力,既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更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在学理层面,笔者以为,争论先有政治文化[9]还是先有政治体制[10],犹如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似乎是无意义的讨论。因为中国的现实表明,3C文化与政治体制是互为因果又相互制约的。例如,儒家思想虽植根于中国春秋时期的封建制度,但随后的中央集权将儒家思想发展成儒家文化,使之成为规范、设计和发展集权体制的指南和依据;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的集权体制既得益于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又吸纳了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文化,从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极权制度,进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毛时代政治文化;当下的权力资本文化更是权力资本经济和政治结合的产物,它推动着权力的进一步资本化以及资本的进一步权力化。
二、西方公民文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区别
为了深刻认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有必要讨论西方公民文化的内涵,作为文化比较的参照。公民、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等概念均属西方舶来品。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区别于奴隶,代表着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洛克、卢梭等人在17世纪所阐发的天赋人权论促使公民一词在西方普及。[11]大致而言,建立在公民和公民社会之上的公民文化具有下列三大核心概念。
第一,公民文化注重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这是公民文化的第一要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公民立身存命之本,也是公民力量的源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最集中的体现是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没有民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自由,而且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和摆设;同时,民主的必要条件是自由,没有自由的民主是一种假民主。所以,公民文化的精髓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和民主的三位一体,公民拥有天然的言论自由、充分的监督权利和受到法律保障的民主选举权利。[12]为了体现这些自由、权利与民主,公民社会必须形成一个公共领域,使人们得以享受共同的资源和共同的机会。[13]公民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组成、所形成的一个公共领域”,这些公共领域为各非政府组织和民众提供了交流观点与协调行动的空间;[14]只有言论交流而没有行动,那只是“魏晋式的清谈”,而只有行动却没有沟通的平台,那有可能是民粹式的盲动。
与公民的权利相适应,公民文化追求平等、反对特权。由于公民即是自由民,所以公民应该而且必须彻底摆脱人身依附、政治依附、血缘依附和地域依附,不仅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追求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由从可见,公民文化奠基在领袖与平民的人格平等、同志和异己的相互尊重、胜者与败者的和平共处之上。[15]为了用制度来保障这种平等,公民文化提倡程序正义、手段正当,坚持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追求法治与宪政,提倡价值理性而淡化以目的为依归的工具理性。[16]公民社会能够产生平衡看得见的政府权力和看不见的市场权力的第三元力量;也能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和市场之外的第六权力中心,因为当行政滥用权力、立法偏袒强权、司法有失公正、媒体不能伸张正义、市场漠视责任与道德之时,公民社会所培育的行业协会和民间力量就能有效地填补公平、公正、道德、舆论和市场的五重缺位。[17]
第二,公民文化注重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充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18]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包括体制参与(system as general subject)、投入参与(input object)、产出参与(output object)和自我参与(self as active participant)。[19]有学者根据意大利的情况,用读报率、社团活动参与率、公民投票率等指标来反映公民参与的数量和质量;[20]社区服务、义工精神和募捐习惯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标志。消极参与、有限参与、厌倦参与、害怕参与和放弃参与都是公民文化残缺的表现,也是公民与臣民的主要区别。
所以,公民文化希望通过参与达到公平、公正与关爱,并孕育互助、合作、和谐的文化习惯,[21]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参与其实也是一种责任,与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价值是一体的两面。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就是这种参与的民主体现。[22]Keith Faulks因此认为,公民一词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欢迎,“因为公民包含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成份”,自由主义喜欢公民是因为公民主张自由与权利,保守主义喜欢公民是因为公民包含了责任与义务。[23]
第三,公民文化追求宽容,包括政治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和贫富宽容。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公民之间只有彼此接受和尊重差异,提倡求同存异、理性平等、对话沟通的文化精神,[24]才能发展出一种共同公共品(common public good)的概念和精神,从而追求共同的利益、追求最大公约数,提倡公民文化的共同性、公共性和公益性。[25]而且,在追求这种宽容与共性之时,其基本原则是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追求双赢,赢者不通吃、输者不失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不同利益集团冲突与较量的底线。
毫无疑问,这种公民利益的共同性与集权社会的一统性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是通过民主投票和平等协商的机制来反映多数公民的意志,并可以通过持续、经常的沟通,不断改变和改进不合时宜的决定,保持公民的共同性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和充满活力的过程;而集权社会的一统性是通过强权与强制,迫使公民展示共同的意志,缺乏外部对话和内部协商的机制与平台,而且是一锤定音,充满僵化。[26]
上述西方公民文化所体现的个人自由与平等、社会参与以及宽容、理性等三大理念与精神,与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以下简称2C文化),存在非常明显的反差。2C文化浩瀚无边、差异极大,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意思的是,2C文化与西方公民文化相比,虽然有着惊人的滞后性,但无论是内外战争、政权更替、天灾人祸、政治革命与经济变迁,都无法摧毁2C文化的顽强存在与延续发展,而且它们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和一致性。
总体而言,2C文化在下列三大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共性,并与西方的公民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一要素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旨在维护等级秩序,提倡社会稳定。儒家文化提倡国家优先、集体为重,个人服从家庭、家庭服从国家,大一统文化是儒家的理想。在此一元政治和一统社会的影响下,传统中国只有宗族社会,没有公民社会,是一种地域性、血缘性和依附性文化的综合,其政治文化特点是一种臣民文化,与公民文化截然不同。[27]
表面上,先秦以来出现了所谓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等,[28]但整部《孟子》找不到关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民参与和平等宽容的只言片语。对此,萧公权认为,孟子的“民贵”之说与近代民权之论不同,因为民权思想提倡民享、民有、民治,而孟子的“民贵”和民意之思想根本没有反映民治的原则;也就是说,对民众可以尽量地表面上尊重,但绝不可实质上信任,更不能与民众分享治权,政治的权力只能而且必须由“劳心”之阶级来控制。同样,虽然清初黄宗羲提出了“贵民”思想,其核心不过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旨在鼓吹地方力量制衡中央君主的权力,对个人的权利和民众的参与仍然排斥,萧公权认为,黄宗羲既反君主专制,也反民众参与。[29]
必须指出,在本质上,儒家文化主张一元和等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权威的至高无上,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压制任何可能的民众反抗与社会动乱,由此孕育出中国传统社会“稳为先、变为次”、“快稳慢变”的文化和社会认知。[30]很显然,儒家文化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有别、长幼有序,提倡所谓的“臣民文化”。中国社会历来喜欢称呼民众为“子民”、“臣民”,从未有过公民理念。[31]《礼记·中庸》说,“子,庶民也”;郑玄注释《礼记》时也说,“子,谓所获民臣”。“臣”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32]所以,在传统的中国,臣民和子民是最低等级,既没有自由,更没有平等。盛行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家族和宗族政治文化所体现的是专制主义的本质,它综合了法古主义、德治主义、家族主义、专制主义等四大要素;[33]而且,“家与国是同构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这样,经过长期的历史教化,宗族观念成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素。[34]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文化将此大一统的集权文化要素发挥到了极致,建立了政(治)社(会)合一的全能体制,导致无处不政治、无人不政治、无时不政治的泛政治现象,各种原有的社会关系,包括宗族、行会、乡社、私人企业等,都被国家权力摧毁和替代。这样,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文化土壤,而个人则失去了家族和社会的保护,不得不直接面对强大无比的国家和政党。由于国家不可能直接控制近十亿的个人,于是便设计和建立了无数个单位、街道、公社、大队、小队,将所有个人强制编入其中,[35]以至于不再有“独立于国家的任何私领域”。[36]
经由这场文化与社会的急剧解构和重构,出现了个人绝对服从组织、组织绝对服从国家、国家绝对服从中共、中共绝对服从领袖的政治文化。而且,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三级组织成为国家的代表,严格控制着个人的自由空间。表面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提倡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却将传统的国家至上发展成中共的一元领导;臣民文化和服从意识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国家利益和中共意志的旗帜下出现了新的形式,对皇权的崇拜发展成对领袖的狂热,领袖成了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朕即国家”的皇权文化成了毛时代中共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共领导人柯庆施曾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37]。于是,“从土改到农业学大寨,一次次政治运动破除了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畏惧,但却为他们树立了新的偶像崇拜。”[38]毛时代的中共文化成功地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文化中的一统文化、一元政治、一种权威和一个领袖。
尽管毛时代的中共文化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家族文化实行了革命性的摧残,但它只是摧毁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政治行为,并没有在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上彻底地清除传统文化。这种政治强制导致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家族文化暂时隐退,并在表面上让位给以党性、阶级性为核心的中共文化,但权威和等级并未实质性解体,不同的只是权威的主体由家庭转化为政党、血缘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奴性演变为党性。毛时代的中共革命只不过是改变了有形的政治制度与物质载体,却并未铲除无形的等级意识和威权文化;毕竟,不惜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和领袖权威是集权统治者永恒不变的准则。[39]毛时代的中共文化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中的秩序、等级和稳定这三种要素,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成功地维护了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相对有效地抑制和控制了社会动乱,防止了政权的更替。[40]
2C文化的第二要素是限制民众参与,推行愚民政策,主张义务本位。传统的孔孟之道是重义务、轻权利。王绍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义务本位的文化, 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文化”,这样,“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之’、‘庶人不议’的主张”。[41]同时,儒家文化主张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由此纵容了独裁政权享受特权、滥用特权,进一步抹杀了个人参与社会公益的权利与自由。那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尽管也有谏言、甚至死谏的传统,其动机不是制衡权力,而是帮助统治者更好地统治人民与社会,他们只是御用的谋士和智囊而已;其本质还是奴性,受到政治的依附心理之支配。[42]
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秩序是“家-天下”结构,或如费孝通所表述的“差序格局”,即以个人为起点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的结构。[43]这种差序格局迫使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的边界模糊化,甚至消失或合一;大组织与小个人的关系既不是“沙拉型”的保持各自的特点与形状,也不是“匹萨型”的互相混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以大代小、以大融小,并由大拥有小、由大庇护小;个人的权利由家庭、宗族、社区和国家予以代表和恩赐,[44]并以个人放弃权利为代价,换取家庭、社区和国家对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如果个人试图挑战权威、争取权利,那么家庭、社区和国家就理所当然地取消对个人或臣民的保护,甚至侵犯和惩罚个人的不敬行为,以防止这种“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之行为产生示范效应和燎原效应。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契约:国家之所以保护个人,以个人必须服从国家为前提;有限的自由和权利只能由国家赐予,不能由个人争取。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文化同样提倡服从的义务,反对个人的权利。当时流行的中山装代表的是一种制服文化,它也意味着利用权力制服(动词)万众。[45]而且,毛时代的中共文化普遍提倡愚民政策,主张知识越多越反动,其目的是先使民众愚昧,再使愚昧之众变成盲从,而愚昧和盲从之众是统治者最容易运用的工具,有助于毛时代的中共领袖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民众当作可用可弃的群氓。在“文革”中,中共领袖既可以发动“红卫兵”参与“打砸抢”,帮助自己夺权;又可以在“夺权”成功后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迫使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离乡背井,防止那些习惯于“造反”的红卫兵影响社会秩序。[46]这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攻武斗”,绝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众参与,而是党国一体的政府行为对民众自由意志、自由选择、自由参与的极大侵犯。所以,在迫使民众轻权利、重义务、轻参与、重服从方面,中共文化与儒家文化如出一辙,只不过中共文化对民众的利用和掌控的能力与手段远远高于传统文化,它既能使民众在“奉旨造反”中感受到“大鸣、大放、大辩论”及打倒“权威”的参与快感,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政府利用的玩偶,而且还深深地为自己“当家作主”而感到由衷的自豪。这就是毛时代中共文化的一大高明之处。[47]
2C文化的第三要素是以暴制暴,缺乏宽容的文化与习惯。中国历代帝王大都更乐于接受法家文化的苛刑严法;为了维护统治,宫廷政治往往不惜手段,残杀异己,充满腥风血雨。[48]在这一点上,儒家的“温良恭俭让”更多地被用于要求臣民对上级官员的忍让、训从和恭敬,而不是一个官民之间、皇臣之间共同遵守的准则。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推行了一套双重标准,即妻子对丈夫要“三从四德”,但丈夫对妻子则可以自由行使夫权压迫;百姓对官员必须“肃静”、“回避”,而官员对百姓则掌握生杀大权。这种所谓的“温良恭俭让”旨在维护君君臣臣的“明尊卑、别贵贱”的秩序,只是一种个人私德的修为和集权者教化臣民的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集权制度下,政治不宽容是一个基本特征,因为这一“朕即天下”的制度体现了权力私有和权力垄断的模式,它在根本上拒绝社会和臣民对权力的挑战、分享和监督。[49]这样,在现实中官民之间、上下之间很难出现宽容的文化。尽管在新朝代出现时,为了疗伤止痛、平息反抗,统治者会普遍实施让步政策,休养生息,但一旦恢复元气,就会变本加厉地实行土地兼并、征收苛捐杂税,最后只能逼迫农民再度起义,改朝换代。长此以往,民众便只认同以暴制暴的效用,而统治者则相信只有更残酷的暴力才能稳定社会、保住政权。这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成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共同宿命。[50]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文化更是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而且将这种斗争演绎成人间的一种“乐趣”与“享受”,即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十年“文革”中,那些在专制文化中长大的“红卫兵”,对待自己的老师、同学和领导,其手段之毒、心肠之狠,一点都不亚于那些专制统治者本身。
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对下是狼、对上是羊;对内是狼、对外是羊;[51]对穷人是狼、对富人是羊;对弱者是狼、对强者是羊。这种狼羊双性完美互换的本质是儒家和中共文化共同推崇的威权理念,它们共同信奉权力本位这一准则:你有权力,我就是你的羊;而我有了权力,你就是我的羊。“专制主义把人变成羊、专制主义又把人变成了狼,这种政治文化惟独不能使人成其为人”。[52]这样,上下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统治者经常以退一步就要亡党亡国的警告恐吓上下,民众则以让一步就要被秋后算账的历史教训来鼓舞坚决不退的斗志。毕竟,官民之间都是在2C文化的浸淫之下长大,都知道退却、宽容只能遭到更惨的灭顶之灾。于是,双方只能竭尽全力,死守底线,同时将对敌人的仁慈视为对自己的残忍。“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中共文化的典型写照。[53]在拒绝宽容、坚决斗争的原则上,中共文化比儒家文化走得更远,因为它结合了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暴力原则,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宽容文化的培育与生长。
基于上述2C文化与公民文化的不同特点,可以发现2C文化与公民文化在总体上是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对此,文化悲观论者认为,中西文化天然排斥、水火不容,“没有健全的私人,就不可能有负责任的公民;没有正常的私人社会,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公民社会”;他们主张中国先要补私民社会的课,才能奢谈公民社会。[54]也有人认为,以社会阶层为特征的中国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公共意识、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的历史觉悟,离具有社会公正和社会关怀意识的公民社会相距甚远。[55]
与此相反,文化乐观论者认为,中西文化可以阴阳互补、合理兼容,而不是对立和排斥;[56]他们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可以“良性互动”,[57]而且认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市民社会”;[58]更有人提出,中国的“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已经出现良性的模糊。[59]
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文化中性论者,既不悲观,也没有如此乐观。笔者以为,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公民文化的兼容与排斥都存在相当难度;中国的政治文化在最近30年确实出现了结构性变异、创造性转化和历史性置换,而且植根于西方的公民文化开始与中国的2C文化发生接触、对话和交流,并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文化,即权力资本文化。
三、权力资本文化的特征: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利的同步增长
中国的权力资本文化可以定义为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结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主观态度、交流符号和理性行为。它既是中国政治文化历史性的变异与逻辑性的延续,更受到了1978年以来中国权力资本经济和西方公民文化的影响。必须指出,这一权力资本文化既与1978年前的2C文化密切联系,又自成一体,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在市场化、全球化、多元化、私有化这“新四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既非苏联式计划经济、也非西方式市场经济,而是具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本经济,这促进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成功地结盟,[60]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激发了权力腐败(受贿)和资本腐败(行贿)的糜烂性、制度性蔓延。[61]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初步形成了权力资本文化,体现出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利的同步扩张,并显示出下列特点。
其一是政治信仰的贫困强化了权力腐败与资本腐败的合流,并促使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有效结盟。[62]儒家文化与中共文化虽然都主张国家至上、领袖至上,但还是主张官员廉洁,贬低资本形象,批评官商勾结;公民文化则提倡个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强调一般德性、社会德性、经济德性和政治德性。[63]但权力资本文化模糊了权力与资本的界限,为资本腐败和权力腐败的蔓延提供了文化保护。[64]
一般而言,政治信仰与物质利益是维系官员对一个政权忠诚的两大支柱。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之所以能防止三年大饥荒时出现陈胜、吴广式起义、能发动常人无法想象的“文革”,主要不是依靠物质利益诱惑,而是通过政治信仰产生强大的向心力,促使官员自觉自愿地效忠毛泽东、真心诚意地相信共产党。与此同时,在革命神圣的旗帜下,贪欲、物欲和情欲遭到了压抑,贪官污吏因此难以大量出现。这就是目前大陆一些民众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们“两袖清风”的背景。[65]1978年以来,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幻灭,共产主义理想成了政治表演当中的道具。[66]为了继续维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向心力,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只能借助另一个维系忠诚的法宝--物质利益,来换取中共官员的效忠,这就是贪污腐败的制度背景。[67]一旦官员成为贪官,依靠中共体制获得了大量的不法利益,他们就与中共政权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中共政权获得了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腐败官员的支持,因为一旦中共政权瓦解,贪官们不但失去了继续捞钱的机会,而且可能失去中共政权的保护而面临制裁;另一方面,腐败的官员们必须以忠诚作为获得特权的回报和代价,紧跟党中央、听命领导人,一旦表现出异心,党随时可能以反贪的名义将他们绳之以法,反贪成了打击异己、巩固政局的有效工具。[68]在现行的腐败政治环境里,官员们所感受到的“潜规则”是:你必须与众人同流合污,成为贪官,因为水至清则无鱼,混水才能摸鱼,个别清官的存在将使多数贪官缺乏安全与安宁,因此清官很难在现存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生存。所以,对中共而言,如果不反腐败,党就失去了保证下属忠诚、控制官员言行的监督手段和威慑力量;但反腐败又不能太彻底,否则官员们不再能通过权力获取利益,自然就不会真诚地效忠政府。[69]
其二,宗教信仰的贫困进一步推动权力与资本的腐败。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相信来生和轮回报应,相信好人好报、坏人坏报,所以当宗教信徒面对物质诱惑、从事恶行之前,首先存在内心的恐惧,顾忌神的惩罚,唯恐来生因此而进入地狱,与魔鬼同行。[70]这种来自宗教信仰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比法律惩罚和媒体监督更能有效地扬善止恶,以内省的形式抑制腐败行为。但中共的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只管生前尽情享受,死后管它洪水滔天,因此贪官们内心毫无畏惧,其行为不知节制,敢于疯狂地吞噬民脂民膏。面对这种有私无畏的贪官文化,法律和媒体就显得苍白无力。当然也有许多中共贪官开始烧香拜佛,但他们大多是假信徒。他们祭拜佛祖的动机有二,一是保佑自己平安无事,继续贪污;二是诅咒政敌和对手不得好死,祈求佛祖惩罚。[71]而佛教的真义其实是普渡众生,无私无欲。那些以共产党人的身份祭拜佛祖的中共贪官,在宗教面前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他们的行为是对神的亵渎。没有宗教信仰的约束,权力资本文化往往表现为无所节制、为所欲为。[72]
其三是权力与资本结合滋生了腐败的商业环境,激发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急速增长。权力和资本对腐败形成了相互激励的需求和供给,在中国这样的经营环境里,连外资都深刻地体会到,投资中国的成功主要不是依赖于单纯的市场竞争,而是取决于对权力的购买。[73]中国开放之初,许多中国学者对外资企业曾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改造中国的腐败文化,强化规则、净化市场,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殊不知,许多外国大型企业一旦进入中国,马上受到中国“酱缸文化”的污染,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与中国的腐败文化融合,出现所谓的“逆向接轨”(不是中国与世界接轨,而是世界与中国接轨)。外资企业往往不惜重金,设立相当规模的公关部门预算,雇佣中国本地的“买办”,实施“以华制华”的战略。[74]于是,资本和权力形成了“良性竞争”态势,只要官员“吃得下”,资本就“喂得起”,“不吃白不吃,能喂尽量喂”;权力资本文化隐含的定律是:官员们“吐出来”(自然是国家和公众的资源)的应当比资本所“喂”的要多得多;官员们今天“吐”得越多,明天资本就可能“喂”得越多。这样,官员的“吃”和“吐”与资本的“收”和“喂”形成了正反馈:官员们“吃”得越多,“吐”得就越多;官员们“吐”得越多,资本“收”得也越多。这种正反馈为下一轮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喂”和“吐”提供了激励和动力。[75]
其四是私人恶权利的扩张。私人权利的存在与发展本来应当以不损人、不犯法为底线,一旦冲破了这一底线,私人的良性权利就质变为恶性权利,即完全背离了公民文化所提倡的公民的基本德性。[76]1978年以来,经济活动的自由是增加了,但在权力资本文化的熏陶下,个人经济活动的伦理和个人行为的道德却逐渐瓦解,而健康的公共利益、公益奉献精神尚未确立,这样正好为不法业主和商人造成了天赐的暴富良机。于是,举世震惊的黑窑事件、毒米事件、毒奶事件等便层出不穷。当基本的道德伦理被权力资本文化摧毁之后,物欲、情欲、贪欲全方位地畸形释放和发泄,拜金、功利、私欲主导了年轻一代的价值体系,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健康发展遭到阻滞。这种现象其实有其历史根源。林培瑞指出:“毛时代的极端‘节欲’与现在普遍的‘人欲横流’之间没有反弹关系吗?毛时代的‘一切为集体’ 和现在的‘一切为个人’也没有物极必反的关系吗?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极力推崇‘卑贱者’和今日的残酷鄙视社会底层的人也没有‘矫枉过正’的微妙关系吗?毛时代的‘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跟今日‘愤青’的狂热民族主义到底有没有令人深思的牵连?”[77]更进一步看,这种植根于极端个人自利的行为模式并不会培育出有利于社会政治进步的政治文化形态,因为一旦国家再度使用强大的公权力体现国家意志时,缺乏道德伦理追求的个人自利文化便立即让位于国家主义和举国体制,这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同步增长的过程中,那些拥有资本优势的经济精英并不乐意利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得到更多、更大的特权,[78]同时渴望与政治权力结盟,积极入党、参加人大政协,甚至直接做官。[79]在这种权力与资本联盟、资本对权力依赖的博弈游戏中,资本只有放弃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利,才能换取资本发展所必须的政治资源、法律保护、盈利机会;而政治权力正是借助这种依赖关系,维持着权力对资本的统治关系,资本自身开始成了权力体系的一个部分,结果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权力对整个社会的控制。[80]这就是前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契约关系。
总之,在当代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环境中生存的资本,不仅屈服于国家权威、阻碍社会多元,而且还希望独占与政治权力所建构的利益共同体。为了资本的利益,权力资本文化鼓励急功近利,尽管这是对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挑战,却无助于推动与催生公民文化所提倡的公民德性和民主社会所主张的选民素质之成型与成熟。尤其是,虽然政治人权力和经济人权利正在不断扩张,但缺乏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本的社会大众的权利并未获得相对应的发展;相反,政治强人和经济富人的权力越大,弱者和贫者的权利便越小,这样的零和游戏效应正是权力资本文化的重要特征。
四、权力资本文化的特征之二:社会参与的有限性
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参与的被动性、短期性和有限性。前述的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习惯于愚民政策,因此阻碍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有时鼓动民众参与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那只是为了“运动”群众的需要。如果说,公民文化鼓励公民在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主动、积极、持续、有效的参与,[81]那么,权力资本文化所容许的是开放一些新的参与渠道(如互联网),有选择(如限制在非政治领域)、有限度(如禁止跨行业、跨地区参与)、有时限(如限定在大灾、大庆典时期)地容忍民众对公共事务表达一些意见或采取一些为当局准许的行动,其本质还是将民众的参与作为巩固权力和资本的工具,只要有利于权力的巩固、有利于资本的发展,就予以开放和鼓励。当然,有时权力也会与资本发生某种矛盾。例如,由于政治斗争或维持经济政治秩序的需要,政府会打击个别行贿的资本和受贿的权力,实行有限的廉政,似乎为公民的真正参与留了一道缝隙和一线曙光。这些缝隙和曙光往往误导文化乐观论者,以为中国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的春天即将到来。[82]其实,权力资本文化下的民众参与与公民文化下的民众参与存在很多根本性区别。
首先,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广泛地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目前最重要的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如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这些权利,都是审批制,而不是登记制。尽管宪法列有明文,任何一个公民似乎都享有这些自由和权利,但在现实中所有这些权利都受种种法律、法规、文件的限制,这些规则的共同特点是对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采取审批制(多数情况下不予批准)。[83]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或由政府创建,或“挂靠”在政府或准政府机构之下(这是相关文件规定的要求),并由这些机构管辖指导。凡是正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无不如此。中国的民间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准政府组织,如官方工会、共青团、妇联、学联等,它们的人、财、物均受政府或中共的直接管辖,实际上与党政机关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第二类是工商联、消费者协会等各种行业管理协会,它们有编制并享有一定的级别,承担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民间社团,如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其负责人大都需要由主管机关认可与批准,而且一些负责人也享有行政系统的干部编制和级别待遇。所以,俞可平认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恰恰与政府的关系最密切,有些直接就是“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84]据中国民政部统计,至2006年12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约32万多个,[85]但绝大多数都属于官方控制和半控制的团体,他们对NGO的干部选举、经费和活动的掌控,导致公民社会的重要标杆—-“结社自由”至今难以实现。已经颁布施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其实严重违反了宪法文字上所规定的结社自由。更荒谬的是,中国是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但过去几十年来,农民不但没有属于自己的农会组织,政府连官办农会都不准成立。[86]对已经存在的林林总总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当局还严格限制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当局一向非常忌讳民间横向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组织活动,同时紧紧抓住对整个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控制,绝不放松。显然,纵向控制越严密、越细致,越显示集权能力的强化,那么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威超越社会和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便越明显,相应地,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空间也就越弱。[87]所以,目前多数全国性的“NGO”,如工、青、妇,都是属于准政府机构,而且还扮演着为政府控制地方性NGO的重要功能;而那些纯民间组织,如防止艾滋病蔓延、环境生态保护等团体,当局绝不允许它们自行发展全国性的组织。[88]
其次,由于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中国的民间组织有机会运用资本的力量,弱化政治权力对民众参与的负面干预。尽管政治权力对各类NGO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但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权力有时候会屈服于资本,为NGO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例如,相关法规规定,所有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必须接受双重领导,一是政府民政部门等主管机关,这是一种名义上的管理;二是业务主管机关,即所谓的挂靠单位,它承担着主要的管理责任。管理上有名无实的民政部门可以向NGO收取管理费,而有责无权的业务主管单位则不能收取任何费用。[89]于是,一方面NGO通过正常和不正常的“管理费”的输送,方便了民政部门批文的获得;另一方面,在日常运作中,挂靠单位由于不能依法收费,便缺乏积极性去监管NGO的“擦边球”行为,有时一些NGO为了排除政治障碍,通过支付本来不需要缴纳的“管理费”,对所挂靠的业务主管机关进行利益输送和公关活动。[90]当然,并不是什么政治风险都可以用“利益输送”来“摆平”的,不能触及当局设定的政治红线或极限,也是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一条潜规则,上述交换只能在灰色地带中进行。所以,权力资本文化下的社会参与只能是有限、有条件和有底线的。除了注册登记的NGO之外,中国目前还存在着200到300万之多的“非法”NGO,它们大都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深厚的政治背景,主要包括在工商部门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海外在华资助组织、海外在华项目组织、海外在华商会以及宗教社团等。[91]这批庞大的“非法”NGO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钱交易,它们在权力资本文化环境下已经成为不是政府的政府,即所谓的“二政府”,成为安排二线干部的场所以及权钱交易的重要载体。[92]
再次,民间社团的功能弱化和空间窄小,以及官方对舆论的严格监管,导致政治权力成功地征服了资本的力量和社会的能量。2008年的“救灾”与“京奥”似乎都证明,市场和资本是功利和无助的,社会是乏力和被动的,只有政府是有力、有效的。在这样的活动中,最大的赢家不是市场、不是资本、也不是社会,而是政府。例如,无论是对2008年初雪灾的救助,还是对年中地震灾害的救助,电视上所看到的救灾主力大都是组织良好的军人、“及时出现”的官员、无处不在的国际组织,却很少见到宗教、慈善和其它的民间团体或民间力量的身影,与1999年9月12日台湾大地震中慈济等民间组织迅速、有效、有力的救灾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3]同样,举国上下为北京奥运的欢呼,正是对政府的动员民众、调动资源、控制动乱、集权决断和筹集金钱能力的喝彩。这次西方社会为了应付金融危机所强化的政府干预措施,似乎也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市场资本和公民社会都已经失灵。[94]
应该指出,在2008年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民众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但他们的参与大多是在政府权力的主导和控制之下,何时、何地、如何参与大多由政府预先作出安排。例如,要求中共党员缴纳所谓的“义务党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08年底的统计,在四川地震救灾中,4,559.7万名中共党员缴纳的“义务党费”高达97.3亿元[95];而且,中央行政指令每个沿海省份包干每一个受灾的县区,实行强制性救济和摊派,这好象回到了“文革”时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96]这样,国家权力充分利用了天灾危机,成功地展现其动员能力和政治高压,压缩了民众自由、自主、自发参与公益事业的空间。这种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更不透明的捐献行为,为权力的腐败提供了新的机会。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救灾工作有14亿元资金的漏洞。当初以为,什么都可能贪,谁敢贪四川地震款?如今已经有人呼吁要“持续盯着灾区”[97]。另外,中国的新闻媒体也是虎头蛇尾,后劲乏力,尽管在四川地震初期新闻媒体作了罕见的全面、迅速的报道,但一旦出现民众对人祸的问责与抗议,中国又回到了媒体舆论一律的旧时代。[98]而且,在北京奥运期间,所有关于四川灾区的报道大都消失和消音,似乎在短短的3个月内,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已经完全没有新闻可报。对此,有人提出需要“重新打响地震灾区的‘抗人灾’战役”[99],但是面对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权力资本文化,这些正义的呼声有点类似唐·吉诃德式的无力与无效。
另外,民间资本与机构在2008年的救灾行动中往往都是一切服从政府的指令。例如,2008年6月20日,《南方都市报》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徐永光提出,四川地震救灾的优先是保持NGO灾后重建项目与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目标的一致性,优先选择政府需要的项目。[100]可见,在中国NGO负责人的宗旨中,与政府保持一致是重中之重。政府需要,NGO就开始活跃;政府不需要或政府反对,NGO就很难活动,甚至难以生存。这样,NGO本身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独立机制,一切以政府的好恶为依归。而且,有些民营资本利用捐款向政府献媚,对于那些不愿捐款的员工或尽管捐了款但并不情愿者,一律开除。[101]
在权力资本文化的环境下,经济资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的参与基本上缺乏兴趣,即使参与了,也是紧跟政治权力的指向或迫于网络媒体的舆论压力。例如,为了防范可能的体制失序和对权力的威胁,权力资本文化并不鼓励民间自发的义工行为和捐献习惯。目前中国只有100多家慈善公益机构,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不到1%,而这些慈善组织所掌握的资金不到GDP的0.1%。而且,公民捐赠主要是迫于政治压力,大多以被动、被迫、短期捐赠为主,主动、积极、长期的捐赠很少。据清华大学一项研究表明,1998年被调查的非赢利组织收入结构中,企业赞助和项目经费占5.63%(居第4位),募捐收入仅占2.18%(居第7位);在回答问卷的非赢利组织中,有34.4%的组织表示没有志愿人员,17.5%的组织其志愿人员为1至4人,只有18.3%的组织其志愿人员在40人以上,此外志愿者平均每人每月参加活动的天数是4.45天。[102]
最后,中国民间参与的意愿十分畸形与变态,反映了中国公民性的不成熟。为了冲破政府权力的长期压抑,中国民众的初始参与行为往往投政府所好(如民族主义);一旦初战告捷,民众的参与行为就会出现“广场效应”,因为民粹主义的情绪遏制了理性判断,而且中间组织又不够发达,[103]其结果只能是无聊的起哄和无谓的内耗。这样,在中共一元化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所孕育出的公民参与,并不具有民主自由的精神,而经常表现为民粹主义和网络暴力。[104]如在四川地震救灾中,网络上针对各种企业和企业家的逼捐之声到处弥漫,出现大量的“人肉搜索”和“网络恐怖”。这是以侵犯他人的自由选择来逼人参与,也是目前网络“愤青”的变态与畸形的写照。[105]此外,中国还有些人时常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呼唤“狼性”的复苏,鼓吹“圣战”。其实,这种狂热正是长期为奴的变态,反映了小人得志、精神分裂的倾向,以及借此掩盖自己虚弱无能、没有自信的心态。[106]这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严重遏制了民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发育。
当代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有国民性和国民意识,缺乏公民性和公民意识,而国民意识多半是国家权力操纵下的民族主义的翻版。例如,在3.14西藏事件中抵制法国超级市场家乐福;在四川地震救灾中抵制日本救援,在网络上高喊“绝不允许日军踏入国土”、“日本畜生怎么可以进入中国”;[107]在5.19国殇日举国致哀之时,众多民众竟然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加油;而在牵涉到众多学生因校舍倒塌的人祸事件发生时,却无法形成象抗议外国人和藏人那样的强度和广度。[108]
中国公民性的弱化和畸形决定了民众权利意识的淡薄,由此影响了中国民众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导致“政治权利的行使,在政治权力的牵引下,流向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权力运行和配置中,反而增强了政治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109]。这样就注定了中国的权力资本文化不可能生长出一种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共和制度的公民政治文化。尤其是由于公民社会的不发达、政府的腐败、单位的不作为、舆论的不独立,导致公民有难只能去找黑社会。目前中国黑社会的发达,就是因为传统专制文化的盛行和政府的强势,以及健康的公民社会难有发展的空间。[110]公民社会是一个舶来品,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也是西方的话语,它们都难以在中国的3C文化中内生;而这些舶来品一旦与中国政治文化结合,就会产生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性”,甚至是公民的劣根性,例如黑社会,这也是柏杨所称的“染缸文化”的体现。[111]这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异化或变异,好的外来种子,如果没有合适的本地土壤和气候,不仅难以生存,而且有可能变异成有害植物。
五、权力资本文化的特征之三:社会政治宽容的选择性
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第三个特征表现在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之间实现了和解与宽容,但这种宽容并未扩展到非权力与非资本领域,所以是有限、有度、有选择的“宽容”。
其一,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标志着权力与资本实现了和解与谅解,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开始淡化。由于允许资本家入党、进入人大政协、甚至直接做官,权力与资本实现了法律和政治上的结盟,由此也扩张了政治权力的宽容限度,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儒家文化贬抑资本和商业的传统,“君子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始合流;同时也颠覆了毛泽东时代中共文化“兴无灭资”的政治口号,更全面修正了中共这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本质。[112]这种权力宽容资本的国策,也让人们对中国政府或许会宽容其它事件和团体产生了希望与遐想,既然过去的阶级敌人、革命对象都可以与之结盟,那么,似乎自然可以期待中国的政治文化由此发生本质的变化,逐步认同公民文化的普世价值。但事实上,现有的权力资本文化所表现的宽容只是有限和有选择的,西方公民文化中的宽容要素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要素相结合,只能孵化出不伦不类的“和谐”政治文化。
其二,政治权力的宽容程度十分有限,宽容的标准很不一致。公民社会是一种自治的秩序、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则崇尚一元政治和一元文化,并由此衍生出与一元政治文化相适应的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它们大多以官位和权力来界定人际关系的尊卑。基于这种一元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很难产生和发展出人与人之间、成功与失败者之间的平等和宽容文化。[113]例如,在四川大地震的日子里,人性精神和人本文化空前展示,全社会也展现了珍爱生命、敬畏生命的力量,[114]似乎大家再也没有“亲不亲、阶级分”的毛泽东时代中共文化的劣质遗传,“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毛泽东时代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开始变得模糊。但是,一旦有人通过揭露大批校舍倒塌、大量学生死亡的事实挑战权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之时,权力与媒体就不能宽容此类言论了。[115]同样,当举国牺牲兴办北京奥运之时,政府可以默认不同政见者对奥运的正面欢呼和积极奉献,开放外国记者相对自由的采访,似乎显示了和谐的诚意,模糊了敌我的界限;一旦出现“不友好”的批评,政府对藏独、疆独和海外民运力量的打压仍然是毫不手软、毫不留情。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十分“勇敢”地在北京设立了示威区,却又十分滑稽地从不批准任何要求游行的申请。[116]
其三,资本难以对劳动实现宽容。权力资本文化主导下的中国社会已开始用专制的企业或资本文化取代儒家的家族文化和中共的单位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民众虽然摆脱了家长和单位的专制控制,却陷入了企业资本的专制管理。目前的中国资本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推崇的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残酷竞争、贪得无厌、零和游戏。山西黑砖窑事件深刻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和无情,为了追逐利润,根本没有道德底线,更谈不上资本对劳动的宽容和忍让。[117]同样,在这种零和游戏下的劳动者也难以做到温良恭俭让,面对资本恶意拖欠工资,民工们只能奋起抗争,甚至暴力相向。[118]于是就出现了劳动与资本势不两立的政治文化;而资本深知,只有得到权力的支持,才能有效地镇压劳动的反抗。权力和资本在这方面的勾结,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加深了资本对政治权力的依赖。[119]
其四,中国的权力资本文化是一个既缺乏公德、也缺乏私德的文化。公德的基础是私德,整体公民的觉悟取决于无数个人私德的品质。私德的底线是不做损人不利己的蠢事;同时,基本的私德要求取官、取利、取名要有道;即便不能做到积极的公民性,至少应该遵循消极的公民性。[120]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私有资本文化,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文化,再是“一切交给党安排”的中共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全球化、多元化、私有化这“新四化”。于是,私欲在没有私德约束的状态下膨胀,诚信成了专责他人的工具,“不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公共生活中,甚至在家庭生活中,最起码的信任都成了稀缺品。人果然成了主流经济学所设想的‘经济人’”。[121]私德本是公德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石,私民培育公民,私德促进公德。不懂孝敬父母者,如何才能效忠社会和国家?不能尊重朋友者,如何尊重他人和社会?不愿宽容家人者,如何宽容社会与政敌?很显然,经济硬件可以超越,但文化软件很难超越。如果试图将中国的臣民文化绕过私民文化,直接跨越到公民文化,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建立在如此缺乏私德的文化环境下的资本社会,只能是有资本而无社会。如果个体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那么,奢谈人与人之间的谅解、理解、宽容与和谐,奢谈公民社会的参与和奉献,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了。而且,在这种权力资本政治文化背景下,任何正常的公民行为都会被质疑为动机险恶。例如,2006年,一位南京青年由于搀扶老人,导致老人受伤,并被老人告上法庭,而法庭的结论竟然是,根据“常情”年轻人面对老人有难应该是无动于衷,而不是见义勇为,因此判定年轻人有罪。[122]同样,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有爱心、但少有爱行的文化,民众既没有长期捐款的文化习惯,而且对好捐乐施者充满猜疑、打击,所以,“在道德荒漠中,是没有公共之善可言的。”[123]
其五,宽容的重要条件是遵守以人为本的基本准则,但中国目前的政治文化现实很难做到以人为本,却很容易做到以权为本、以资为本。以人为本的实质和前提是不分男人女人、穷人富人、好人坏人,只要是人而不是动物,一律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实行没有阶级、国籍、地位和财富偏见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经济资本是很难不歧视穷人和女人的,而政治权力也必须对“好人”“坏人”进行严格区分,坚持鲜明的党性和政治性。[124]例如,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对平民的死亡泪流满面,可以与艾滋病人握手,却不能与政治上地位敏感的老上级“相逢一笑泯恩仇”,甚至在昔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去世时仍然不闻不问。很显然,中国现有的政治文化决定了对政敌的宽容还是一种奢望。有学者呼吁,2009年建国60年之际来一次大赦[125],这也许是对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一种测试,也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宽容程度的一次检验。
所以,在权力资本文化环境下奢谈社会和谐,似乎是一种空谈和游戏。按照正常的逻辑和现实的惯例,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合作境界。在和谐之前,冲突双方必须达成和解;如果拥有权力的一方没有能力、没有意愿、也没有胸怀解决一系列历史的恩怨,那么,所谓的和谐只能是空中楼阁。很显然,目前的政治权力还没有能力和意愿去触碰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权力资本文化决定了中国社会尚未培育出宽容、让步、和解的文化。这种和解与和谐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众参与才能可持续、可巩固。正如范时杰所说,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如果只照搬制度,而没有相适应的文化,那么“在权力配置过程中,政治权利只能是一种被利用的幌子,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国家威权主义”。以村民选举为例,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和民主文化予以配合,没有宽容、守法、公平、多元等核心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灵魂,那么,权力就难以有效制衡、利益难以公平分配、冲突难以多元整合,[126]而且可能出现民主选举与民主意识互相分离的奇特现象。[127]
虽然权力与资本之间实现了宽容,但它们远没有实现对非权力和非资本的宽容;政治权力对异己力量的宽容非常有限,经济资本的傲慢也是处处存在。必须指出,在宽容这一点上,儒家文化主张选择性宽容,即下对上、贫对富、民对官的宽容;中共文化则绝对排斥妥协和中庸,坚持斗争哲学和专政原则;作为对比,权力资本文化则是主张选择性和有限度宽容,即实现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宽容。
六、结论
通过对中国3C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比较分析,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3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本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历史演变的一个短暂插曲?还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固有特性的长期存在?如果认同线性思维的逻辑,就会认为权力资本文化只是中国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向西方公民文化过渡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运用三角思维,重新反思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与未来,也许能得出不同的看法。
表1、3C文化比较
儒家文化(C1)中共文化(C2)权力资本文化(C3)
个人权利次少最少最多
社会参与最少次少最多
社会宽容次少最少最多
表2、2C文化、公民文化与权力资本文化比较
儒家与中共文化(C1 & C 2)权力资本文化(C3)公民文化(C4)
个人权利最少次少最多
社会参与最少次少最多
社会宽容最少次少最多
首先,三角思维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三角的,它将事物一分为三,而不是一分为二。[128]运用这一思路,中国政治文化可以通过两个三角予以理解。第一是将3C文化理解为一个三角的整体,儒家文化(C1)、中共文化(C2)和权力资本文化(C3)分别代表一个角,它们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第二是将2C文化(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权力资本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Civil Culture, C4)理解为三个不同的角,这样就能更清晰地理解权力资本文化的定位和特征。若将个人权利、社会参与、社会宽容作为三个参照和变量,则可以比较不同政治文化的价值、态度和符号。(见表1和表2)
其次,三角思维与线性思维的最大不同是淡化了政治文化的价值判断,强化了功能判断。在线性思维指导下,线的左端就代表落后和错误,线的右端则代表进步与正确,在此线性光谱上,是非对错十分清楚。而三角思维则将三种不同的文化定位在3个不同的角,由于除了左角、右角以外,多了一个上角、小角或斜角,这就排除了进步与落后这一简单的二分法,导致三种文化的定位与定性出现积极性模糊和错位。其实,政治文化本身不宜用好文化或坏文化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文化的独特性十分鲜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而是民族文化;同时,文化的功能也十分重要,也许公民文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但如果公民文化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领袖运用错误的方法,强制运用于水土不服的国家,有可能产生文化灾难。政治文化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功能,而不是价值,因为正确的文化不一定就是有用的文化。
再次,三角思维给中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第三种选择。除了集权文化(如2C文化)和民主文化(如公民文化)之外,三角思维能够帮助人们理性面对中国的权力资本文化,并表明西方的公民文化或者中国的孔孟之道都不一定是中国未来政治文化的唯一选项。发展的不确定和目标的多样性能激发文化的创新力,如果全人类都要迈向单一而既定的共同目标,这既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也是一种文化的宿命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但个人的爱憎立场不应该取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存在。过去30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孕育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权力资本文化,这一新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植根于儒家文化、中共文化之中,并受到西方公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与其它3C文化(儒家、中共和公民文化)一起构成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现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中国政治文化,有可能不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而是一种相对长期和独立的文化形态。
最后,三角思维有可能揭示一种循环发展的文化模式。如果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如果文化发展有可能排除线性的发展(既不是直线、曲线,也不是抛物线),那么封闭的三角有可能促使三种主要文化要素的发展不断循环与重复。如果中国政治文化的三角是集权文化、权力资本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话,那么,它的未来发展有可能在三者之间循环重复,它的下一站有可能是公民文化,也有可能再度重复集权文化;如果中国政治文化的三角是儒家文化、中共文化和权力资本文化的话,那么,它的下一站有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复兴或者是中共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循环与重复犹如时尚和时装的流行,它有可能不是波浪式前进,也有可能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可能在循环中更新,在重复中寻找新的动能和合适的定位。在哲学意义上,循环与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倒退,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太阳不可能永远高升,只有今天的日落才有明天的日出。
总之,中国的政治文化既是一种意识、态度、价值和观念,也是一种符号和象征,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和体制,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所内生的一种独特政治文化。
【注释】
[1]Gabriel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18 (August,1956): 391-409.
[2]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lmond and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 Brown, 1980); Gabriel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Lucian Py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Co. and The Free Press, 1961); Lucian Py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3 (September 1972); Robert Putman, The Beliefs of Politicians: Ideology,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Ital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W. T. Bluhm,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 Richard Wilson, Compliance Ideologies: Rethinking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29) (1977): 552-83; Dittmer, “Thought Refor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Symbolism of Chinese Polem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1977): 67-85; Stephen Chilton, “Defining Political Cultur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1 (September 1988); M. Edelman, The Symbolic of Politics, 5th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2); Edelman, “Skep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the Media, and Mass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1988): 1333-39;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London: Fortana, 1981).
[4]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1987): 3-21; Wildavsky, “A Cultural Theory of Leadership,” B.D. Jones, ed., Leadership and Politics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9) Ruth Lane, “Political Culture: Residual Category or Gener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October, 1992): 362-87.
[5]Shiping Hua, “Introduction: Some Paradigmatic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Shiping Hua, 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989-2000 (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5-9.
[6]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Ethics, 104 (2) (January 1994): 352-81.
[7]有关权力资本经济的定义与特征,参见Zhaohui Hong:“The Role of the Power-Capital Economy in Chinese Reform,”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Fall 2002): 1-16.
[8]Brian Girv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Liberal 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 John R. Gibbins,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89): 31-35.
[9]认为先有政治文化,后有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学者和著作有: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1988): 1203-30;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ichard Merelman, Partial Vis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Robert Putman,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认为先有政治体制,后有政治文化的代表学者和著作有: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337-64; Gui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eds., Transitions from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1986); Mitchell Seligson and John Booth,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Type: Evidence from Nicaragua and Costa 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1993): 777-92; Edward Muller and Mitchell Seligson,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94): 635-52.
[11]高楼居士等编,“公民文化”(http://baike.baidu.com/view/889225.html),上网日期:2007年6月1日。
[12]Keith Faulks, Citizen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56-65; Derek Heater, Citizenship: The Civic Ideal in World History, Politics, and Education (London: Longman, 1990).
[13]Boulding Elise, Building a Global Civic Culture(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
[14]陈健民,“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9日。
[15]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Christopher Pierson, Chris Pierson, and Francis G. Castles, eds., The Welfare State Reader (England: Polity, 2006), 30-39.
[16]曾盛聪,“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学海》,2005年第2期。
[17]出处同注14。
[18]Michael Walzer, “The Civil Society Argument,” in Chantal Mouffe, 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Verso Books, 1992), 89-107.
[19]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11-26.
[20]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
[21]出处同注14。
[22]俞可平,“协商民主: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662),上网日期, 2006年8月11日。
[23]Faulks, Citizenship ,1.
[24]Charles Taylor, “Shared and Divergent Values,” in R. L. Watts and D. G. Brown, eds., Options for a New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陈健民:“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
[25]Boulding Elise, Building a Global Civic Culture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8),1.
[26]甘绍平,“公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学习时报》第200期 ,2003年9月。
[27]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28]商灏,“从SARS到汶川地震:一个公民社会的成长”,《华夏时报》,2008年5月17日。
[2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页8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 卷,页560;引自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4期 。
[30]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32]出处同注11。
[33]叶娟丽,“试论我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历史特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引自彭庆军的“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363),上网日期2008年6月24日。。
[34]彭庆军,“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出处同上。
[35]秋风,“没有私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空中楼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5日。
[36]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理论参考》,2006年第2期。
[37]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31,引自彭庆军的“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出处同注33。
[38]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204,引自彭庆军的“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出处同注33。
[39]彭庆军,“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出处同注33。
[40]Michael Schoenhals: “Political Movements, Change and Stabil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pecial Issu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50 Years (September, 1999): 595-605.
[41]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出处同注29。
[42]唐昊,“中国政治文化:狼与羊的‘完美’结合”,21CN网,(http://news.21cn.com/luntan/retie/2006/10/18/3005192.shtml),2006年10月18日。
[43]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页25。
[44]潘修华,“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建设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
[45]朱大可,“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凤凰电视“世纪大讲堂”,2008年9月21日。
[46]Yin Hongbia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of Factions in Red Guard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vember 1996): 269-80; Yixin Chen, “Lost in Revolution and Reform: the Socioeconomic Pains of China's Red Guards Generation, 1966-1996,”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1999): 219-39.
[47]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48]出处同注42。
[49]Walter H. Slote and George A. De Vos, 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SUNY Press, 1998);俞睿,“政治宽容: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演进的理性诉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50]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51]出处同注42。
[52]出处同注42。
[53]A. Liu, “Looking Back at Tiananmen Square,” Peace Review 12 (1) (March 1, 2000): 139-45.
[54]出处同注35。
[55]范时杰,“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阶层与中国权力配置”,引自范时杰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演讲(www.bnusgl.com/Item/2170.aspx),2007年9月29日。
[56]甘阳,“民间社会概念批判”,张静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57]参见邓正来的“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卷(总第15期);邓正来,《国家与社会》,载张静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市民杜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创刊号。
[58]俞可平序,“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形成,需要社会管理体制革新”,侯伊莎著,《激活和谐社会的细胞——“盐田模式”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7年)。
[59]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60]洪朝辉,《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纽约:柯捷出版社,2004年版)。
[61]Gong Ting, The Politics of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62]Julia K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New York: M.E. Sharp, 1997).
[63]William Galston, Liberal Purposes: Goods, Virtues, and Duties in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1-24.
[64]Jean Louis Rocca, “Corruption and Its Shadow: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Corrup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2): 402-16.
[65]F.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Xiaobo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a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4-53.
[66]Xiaobo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 154-89。
[67]Gordon White, “Corrup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March 1996):149-69.
[68]Xiaobo Lu, Cadres and Corruption, 190-227.
[69]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Lawrence Harrison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80-97.
[70]K. Hughes, Religion in China (Florence, Kentucky: 2005).
[71]Kim-Kwong Chan: “Religion in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me Scenarios,”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33 (2) (June 2005): 87-119.
[72]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3]Bruce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ove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157.
[74]Stephane De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Economics of Planning 31(2-3) (May 1998): 175-94.
[75]Andrew Wedeman:“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rrup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42) (February 2005): 93-116.
[76]Amy Gutmann, Democratic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en Macedo, Liberal Virtues: Citizenship, Virtue, and Commu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7]林培瑞,“应该反省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开幕词,见《争鸣》,2008年11月号,页3。
[78]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9 (1) (Spring 2004): 32-45; 贾西津,“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与前景”,2008年2月29日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引自“天则双周”(www.unirule.org.cn/SecondWeb/DWContent.asp?DWID=393),上网日期2008年3月3日。
[79]Bruce Dickson and Marian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February 2000): 87-112.
[80]出处同注44。
[81]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82]苏力、高丙中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法律环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83]出处同注81。
[84]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
[85]出处同注58。
[86]杜光,“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2008年6月28日在“公民社会成长与中国治理改进”研讨会上的发言,(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444),上网日期2008年6月30日。
[87]出处同注44。
[88]周志忍等编,《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89]出处同注84。
[90]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91]王名,《清华N GO研究丛书》“绪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92]萧功秦,“国家、社会与转型”,《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16期。
[93]田旭,“中国非营利组织行为分析”,《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页4-6。
[94]韩西林,“市场经济——还要吗?”(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0922),上网日期:2008年9月21日。
[95]崔鹏,“抗震救灾款物管理有6大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
[96]孙仲,“向地震灾区捐款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21日;刘剑飞,“强制捐款的弊端”(http://txy.nynews.gov.cn/Article/rp/200805/23913.html),上网日期2008年5月15日。
[97]梁文道,“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1205),上网日期2009年1月10日。
[98]章立凡,“地震中的改革大厦—三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引自“多维博客”,(http://blog.dwnews.com/?p=43362),上网日期2008年9月30日。
[99]童大焕,“重新打响地震灾区的‘抗人灾’战役”,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0867),上网日期2009年1月2日。
[100]包颖,“南都公益基金会:有限资金调动百倍的资源”,《中国社会报》,2008年8月11日。
[101]孙嘉夏,“不捐款就滚蛋”(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5/22/content_8225690.htm,上网日期2008年5月22日。
[102]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六期。
[103]出处同注92。
[104]张骥、冯冬蕾,“网络恐怖主义产生原因、特点及危害性分析”,《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页6-10。
[105]萧功秦,“国家、社会与转型”;关世音,“巨额捐款的企业和富豪遭遇精神地震”(http://bar.hexun.com/d/4552259.html),上网日期2008年5月23日。
[106]张闳,“《狼图腾》:‘文化食腐者’的精神盛宴”,《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25日。
[107]李筱峰,“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国政治文化”,“绿色和平电台网”,(http://www.greenpeace.com.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view&id=213&Itemid =33),上网日期2008年6月17日。
[108]出处同注98。
[109]出处同注55。
[110]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年第一期。
[111]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百姓半月刊》(香港),1984年11月15日。
[112]王孔瑞,“浙民企老板入党潮:当‘资本家’遇到党支部”,《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9月6日;孙传炜,“中共修改党章 ‘资本家’可入党”,《联合早报》,2002年11月15日。
[113]贾西津,“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与前景”,出处见注78。
[114]丁松泉,“从珍爱生命的共识出发构建健全的公民社会”(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269),上网日期2008年6月13日。
[115]齐之丰,“四川教师曝光豆腐渣学校竟被劳教”,“美国之音网站”(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07/w2008-07-30-voa68.cfm),上网日期2008年7月30日。
[116]李肃,“奥运示威区故事:该相信谁”,“美国之音网站”(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08/w2008-08-20-voa87.cfm),上网日期2008年8月20日。
[117]王玉初,“当代‘奴隶’拷问了什么?”《广州日报》,2007年6月11日。
[118]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蔡崇国,“温家宝的挫败”,“BBC中文网”(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420000/newsid_4420900/4420946.stm),上网日期2005年11月9日。
[119]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120]Norman Barry, “Markets, Citizenship and the Welfare State: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in Raymond Plant and Norman Barry, eds., Citizenship and Rights in Thatcher’s Britain: Two Views (London: 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1990), 45-53.
[121]出处同注35。
[122]蔡方华,“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太反被告引发的法理之争”,《北京青年报》,2007年9月7日。
[123]出处同注35。
[124]俞睿,“政治宽容: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演进的理性诉求”,出处见注49。
[125]季卫东,“2009国庆,何妨宣布一次大赦?”《财经》,2008年12月2日。
[126]出处同注55。
[127]Zhaohui Hong, “Three Disconnects and China’s Rural Election—A Case Study of Hailian Villag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January 2006): 25-37.
[128]Zhaohui Hong, “The China Uniqueness—Puzzl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China’s Development,”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6 (1) (Spring 2005): 9-10.
党国困境与可能的出路
北山
近来浏览网上有关政治思考的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中国应走民主宪政之路,且分析有理,建言有据。忧的是执政党对上述呼吁少有反应,更有不少论者公然祭起“文革”大旗来否定改革,以毛氏禁锢来否定邓氏开放。执政党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此种谬论亦不作反驳。可见在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已30周年的时候,中国确实是陷入了某种困境。因为执政党实行的是一种以党治国的理念和以党治国的体制,不妨称之为党国困境。这种困境困在哪里?以一个正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来打比方:他的右腿已经踏在了一块坚实的石头上了,而左腿还深陷在淤泥之中;一条腿已走到了现在,一条腿还停留在昨天;拔不出昨天那条腿,就无法走向未来。而拔不出左腿的原因,是因为过去的意识形态之鞋还紧紧地箍在脚上,脱不掉便迈不出步。当年的决策者不肯拔出那条腿,或许是因为前腿立足未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乃为大局稳定所计。可当改革的右腿终于迈出并且站稳了立脚点之后,却发现滞后的左腿难以拔出了。倒退虽不可能,前进也被死死拖住,于是便形成现在进退失据的局面。
有一个说法深得我心,改革就是纠错。原来无错,何需改革?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立论,从权宜之计来看,减少了当年党内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但从长远看来,却预留了一个矛盾:似乎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都是合理的。现在回头再看,其实合理的只能有一个。如果“四个坚持”是对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如果改革开放是对的,“四个坚持”就是错的。这是邓小平这个伟大人物的历史局限。
那种两者都对的官方认可,造成了现在的两难处境:既不能放弃由邓氏推动的改革开放,又不敢否定改革之前的毛氏道路。其结果使得改革派举步维艰,“文革派”却能捡起毛这根棍子对改革派口诛笔伐。而当局的态度甚至退到了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认识之下,在中宣部掌控的所有媒体上,连讨论历史真相和反思文革都成了禁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某些人士对改革开放的攻击甚嚣尘上,把现实社会所有的弊病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现在社会上的诸种不合理现象大多是领袖专制的后遗症,却被思想糊涂之士和别有用心之人当作民主政治的传染病来加以攻击。肯定毛,否定邓,已成为被极左派推动的一股思潮。
毛泽东所发起的一系列以革命为名以整人为实的政治运动,可以被有些人认为是罪,也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错,但是绝不能被堂而皇之地认为是有功!如果对“文革”的否定在当政者的默许下被再次否定,那么中国极有可能再次落入“文革”的轮回。虽然中共官方已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中表现出清醒的肯定态度,但同时如果仍然未敢对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做出清晰的切割与否定,那么事实上等于是在对改革开放的反对派授之以柄。
我们已经看到和能够想象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三个台阶:阶级斗争和领袖独裁的过去;改革开放和一党治国的现在;深化改革与宪政民主的将来。我们现在正站在第二个台阶上。也正是在这个台阶上陷入了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在理论层面上,是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双重合理的困境;形象地看,是前进与后退的劈腿。在现实政局中,是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放手,公民社会难以进入的困境;形象地看,是宪政要求与一党治国的劈腿。那么出路何在?在理论上,需要像3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再一次辨明是非。这就要求中宣部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中央的宣传部,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成为社会言论管制部。而在现实操作上,要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在释权于众,归政于民进程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减少既得利益群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为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应采取有序淡出和逐步替代的办法,来防止前一政体的突然死亡。
改革开放受到诸多左派攻击的原因是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恰恰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放弃现有地位才形成的。但是,过去穷人革命推翻富人统治的暴力方式既不可行又不现实。于是,选择只剩下两种:一种是坚决不改,能拖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另一种是设计一条渐进之路,让既得利益者基本保住现有利益,但是阻断这种利益获取方式的世袭延续,同时让弱势群体逐步改善其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在这一、两代人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的将来,让下一、两代人在公平公正的场地上去进行他们的政治竞争、制度完善和对执政者的选择。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我认为,与其坚持到底,不如光荣引退。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何不能由人民来决定它的去留?关键是秩序与步骤,应当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孙中山以国民党治国,有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明确进程表。共产党为国家民族计,是否也应该对此有所设计呢?
30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的进步不可否认,从几乎等同于君王世袭制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进步到领导干部退休制;并从前任对后任的直接指定,进步到了隔代指定。这已和同样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和古巴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上层楼,应该是党的领导的党内选举制—-不是形式上的选举,而是真正的选举。再进一步,则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全民选举。
从人生看,政治的改变有时很慢;从历史看,朝代的书页却翻得很快。秦始皇想建万年基业,却没有料到秦朝二世即亡。列宁和斯大林为巩固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但没有想到苏联只有70年的寿命。和它们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可以预见的时段里看来会比苏联长寿,但也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才能比较顺利地走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28年,是不断革命、运动人民的历史;后32年,逐渐端正了执政党的位置,才是关心人民发展经济的开始。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不惜掀翻了天下重来一遍的毛泽东,也不会想到他的帮派队伍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被颠覆,而他的“文革”路线仅仅过了两年就改弦更张了。“文革”中常说的那句话:“让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现在想来是完全不靠谱的荒唐话,就像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用一个三级跳就能跨进共产主义天堂那样不切实际。况且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江山已经变色,没变的只是党国体制而已。像毛那样的政治巨人倾半生之力来“反修防修”,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谁又能将身后的政治格局控制千秋万代?一个人做不到,一个党同样也做不到。真正能做到的,不过是与时俱进而已。
现在的中国,即使不是大部分人,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尚有可取之处,作为建设理论则基本是空想,而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专制者和专政主义的工具。共产主义的国家形态,在它的策源地已经倾覆;其他勉力支撑的几个样板根本谈不上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引进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才得以改善和发展。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有什么必要非得坚持它直到永远?现在许多左派一口咬定普世价值是由西方舶来因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同样从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就成了中国人永世不可离开的革命圣经呢?没了它好像就要亡党亡国,实在有点危言耸听。
与其坚持一党永治,不如让人民择善而从。如果它真是好东西,相信将来人民还会选择它。人民需要的,只是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主义或特定的领导集团。正如过去的人不能决定现在的是非,现在的人也不可能决定将来的是非。现在党的政治局不可能决定30年后的政治局人选和方针政策,那么为什么不能看远一点,对民意、对世界潮流、对现代政治走向乐顺其行呢?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首先要让某种预置的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党分离,使党真正地成为为民执政的党,而不是挟民服从的党。然后逐步替换,让此党自然完成历史使命,避免剧烈的和暴力的政局替换。党要管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理念。但党的领袖对人民的承诺是一回事,全党上下能否不出腐败、清正廉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另一回事。只有单方面的承诺,没有另一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毛泽东之所以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才使得所有飘在空中的好话落到地上都变成了坏事。
只要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不受制约,那么立党为公就必然成为一句虚言。只要入党能为当官开一扇方便之门,而社会又处在官本位状态,那么入党这个行为就必定是为己谋利的成份大于为民服务。只要入党和升官都是由内部、由上级指定而不是由外部、由下层选举的,那么可以想象被指定的官员首先是对上、对内负责,其次才会对下、对外负责。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无力改变党的执政地位,但又无法完全相信党的执政理念,并且也无法监督和修正党的执政行为的原因。现在党的理念是执政为民,但执政和为民二者是不可能自然相等的。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是,执政党的官员中除了少数具有圣人品质的人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大部分属于凡人的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利己,然后才会去利人。这正是执了政的人不肯让别人去执政的利益所在。只要一党执政的前提存在,入党是为利益而不是为理想也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入党做官,首先成为一个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行为,而且因为只有一党执政,此种自利行为不会得到有效监督。而党这个平台就是一部分人优先获利的温床而不是全体公民公平的赛场。我相信,战争年代入党的人也许是为了理想献身的居多,他们有些人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来参加革命的;但建国后在以党治国的优越地位下,献身的理想被晋升的考虑所取代,申请入党的人们拴在裤腰带上的不再是脑袋,而是钱包了。
如果认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永远不变的一党执政,那么只有这一党完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才可能是真正为了人民的。除此之外,无论是党的宣传,还是党的承诺,都不能保证它首先不是一个自利的利益集团。现在被执政党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真正的关键之处只在于一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改革的底线,无论怎么改,也不能把党的领导地位改掉。而且有党对全社会的控制,便于保持目前的稳定状态。执政党最耽心的是,一旦放权,天下大乱。这不能说只为一党之计,也有为国为民保持稳定的考虑在其中。但是改革推进到了一党执政这道门坎就无法迈步,并且这道铁门永远也不想打开的话,实际上改革就走到了尽头;而开放,就是你只能看着世界在变,自己家里却不能再变了。这就是真正的党国困局。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未必意识不到,但他们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牵扯,欲动不能,欲不动也不能。
作为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走出困境的思路,仅供党的、国家的领导和关心国事的人们参考。如不可取,也算是抛砖引玉。
思路一:党员民选。
既然害怕多党制引起乱局,必须保持一党治国的国体,那么就必须让执政党真正来自于民,服务于民,才能长治久安。这就要求改变目前党员由党组织自身来选择和发展的方式,而改为党员由所在支部范围内的群众选举,并由选民监督。执政党各级官员由党员选举并受党员监督。群众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党员有罢免权。而党员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官员有罢免权。这种办法可以真正保持党员的人民性,同时也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如果人民依然认为共产主义是奋斗目标,则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如果人民不再这么认为了,则可在适当的时候为党改一个更切合实际的名称。
思路二:停止发展党员,逐渐融党于民。
由于执政党已经单独执政60年这个现实,在其他现有的党派并不具备执政实力与经验的条件下,从突然换由其他党执政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计,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只由执政党掌政,担任各级国家和地方职务的执政党官员依旧行使其职权直至退休;但从此不再发展新党员,后继的各级官员,均由所在范围内的民众选举补充,逐步有序地完成从一党政府到多党政府或民选政府的平稳过渡。当所有共产党员因自然规律而不是政治斗争退出历史舞台时,也就是执政党光荣宣布已经完成了为人民打下江山并把江山交给了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个党的生命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结束,而是自然地融入了人民之中。
可以想见的是,这两个思路都会受到党天下思维者的激烈反对,这样不是取消共产党的统治了吗?我想反问一句,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就那么可怕吗?如果认为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就说明这种思维已经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化。任何东西都有开始也会有终结。共产党在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执政的,也不可能执政直到永远。我们的现在终将成为后人的过去。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50年、100年或几百年后,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把它看成一个为了人民解放而成立,在追求人民解放的过程中立下功勋也犯过错误,最终明智地改正了错误,真正用立党为公的精神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人民的政党;还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成立,在追求人民解放的过程改变了初衷,把立党为公变成了立党为党,为了一党的利益坚持掌权决不放弃,直到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不得不失去政权的一个朝代。用历史的眼光看,到底哪一种结局更好呢?
在已经不是君王世袭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历史条件下,不做勇敢的改变,只能使执政党的集团利益一代又一代继续高居于民众之上,这是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劝诫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不是由主义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的制度决定的。而对于现在的当政者来说,维护现有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尚可理解,人总会有自利之心。但是维护数十年后不知道是谁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而不肯改变,就未免短视并且缺乏现实的担当和历史的责任感了。
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既是现在的稳定因素,也是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出路是一党政局的逐渐弱化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其实无论对人民做多大的让步,当政者和民众的地位都不会平等。当政者能够说了算的有很多:制度、法律、政策、與论控制与导向,但人民能说了算的,在民主社会里也仅只一件,就是他们手中的选票。如果连选举的权利也没有,那就只有听从或并不心甘情愿地听从,直到他们有一天不能再忍受,而党国也像清朝末期或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那样再也无法稳定。
当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状况,是中共建国30年来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对无产阶级革命神圣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妖魔化的结果。许多错误认识都源于这个思维定式。当时的全党全民虽然因为对“文革”的强烈不满而渴望变革,但举国上下的思想却很少能越出这一雷池。当政者提出“四个坚持”,是为了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保证执政党地位稳定,才能有序并有效地领导改革开放。就当时国人和大多数党员的认识水平而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合法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是合法的,而资本主义是不合法的。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喊了30年“毛主席万岁”,批了30年资本主义。如果一下子对毛泽东全盘否定,确实会让人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从而引起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但现在情况和环境都大大不同了,因为开放,因为改革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时期,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但是子虚乌有,而且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非万恶之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在改革演进之中,它恰恰是改革开放所需借鉴的主要参照系。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绝不仅仅来自于一场成功的武装革命,也绝不能只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不受检验的理论地位,而应该来源于人民的认可。所以执政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如果这三点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应该继续成为不可触动的党国信条。
如果承认执政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在于民,而不在于党自身,也就不能因为目前正在执政就永远合理合法;只有人民通过选举认可它的执政地位,它才合法--合民主政治的宪法,而不是皇权统治的家法。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死结,就是人民实际上不具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这个结不解开,中国这座大厦的基础就是空的、不牢固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不愿正视并解决基础问题的发展。开放的国际环境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基础的重要性,而我们只愿把楼盖高盖大,却不愿去纠正这个基础的不合理并加以改善。
中国现政权对国家的控制,仅从控制这一点上来说,在现阶段基本维持了稳定,这种体制成功地使任何别的党派和社会群体都无法与政府竞争。但是政府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暴力集团在造反就有恃无恐或高枕无忧。减压、转型,要优于简单地维持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公民社会,把利益、责任,同时也把危险逐步转移到全社会,让社会共享、社会共担,从而和平、有序、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宪政体制中去,这将是全民的福祉,同是也是执政党的福祉。
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与前景
古洪能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一、造成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原因
二、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前景:困境的破解之道
1976年“文革”结束。这场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就是从此刻起,一种比较强烈的政治变革诉求便在民众中产生了。当局出于挽救统治的需要,也因应时势,启动了改革开放。于是民众便在改革开放的名目下,企图推动政治变革。党内的部分开明派也曾响应这一诉求,其顶峰便是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然而,1989年后政治变革冷却下来,直至进入停滞状态。此后,中国大陆便不再有真正的政治变革了,时至今日也未透出一点曙光。现在,无论是当局还是民众,都缺乏推动政治变革的动力,从而使得政治变革处于一种令人沮丧的无所进展的困境之中。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大陆的政治变革是否还有希望?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笔者将运用政治博弈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希望能够发现继续推动大陆政治变革的力量和实现政治变革的道路。
一、造成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原因
目前,大陆的政治变革完全处于困境之中而无法自拔。本来,大陆政治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政治变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铲除这一毒瘤,这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当局却不敢直面这一现实,但又不能不提一些关于政治改革的说法,于是就回避要害,要么空喊口号,要么就将行政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尽管他们都明白,要真正进行政治变革,就必须终结一党专政,但他们也不敢直面这一事实,更不要说采取行动了。在当局与民众分别作出这种选择后,大陆的政治变革当然也就举步维艰,处于困境之中而无法自拔。
如果用政治博弈理论来分析,就可以发现,目前的这种困境就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状态,只不过这种均衡是一种坏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好的状态,故而谓之“困境”。我们知道,博弈意味着参与者(亦称博弈者)在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时,相互之间必须考虑对方的策略选择,由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博弈者往往会理性地按照趋利避害的法则行事。如果博弈者最后所采取的都是在所有可能选项中的最优策略,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策略的组合便构成为博弈均衡。如果从博弈局中跳出来观察,博弈者也许会发现,这种博弈均衡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最坏的选择,而本来大家是有更好的选择的。著名的“囚徒困境”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以此来看,则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状况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困境。因为大陆的政治变革过程就是一场政治博弈,全体大陆人几乎都可以说是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明显地分为两方,或者说两个阵营:一方为有组织的当局,他们以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来参与这场政治博弈;另一方则是无组织的普通民众,几乎全部是分散地、以个体行动的形式来参与这场政治博弈。这两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围绕着政治变革的问题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就造成了目前的困境状态(如图1-1)。
图1-1: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形成 (注:1. 图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博弈者的利益得失预期; 2.图中的粗线即为造成困境的选择路径。下同。)
从当局一方来看,他们的策略选项为:直面症结而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或回避症结而拒绝真正的政治变革。他们知道,如果真正实行政治变革的话,那么自己就很可能成为变革的对象。所以他们很清楚,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变革而维持现状,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对当局来说,不管民众作何选择,他们的理性选择都是回避政治变革。再从民众一方来看,他们的策略选项为:直面症结而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或者回避症结而不要求真正的政治变革。按理说,普通民众往往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有政治变革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因此他们都应该选择前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并未作此选择,而是选择了后者,即回避政治变革。这是因为,在当局决意回避症结而不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如果民众还是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话,那么就会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从所谓的“反右”到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大陆民众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一切行动,都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这便是明证)。所以,完全是出于无奈甚至是恐惧,民众只好选择回避,不再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如此一来,政治变革的困境便形成了,即当局无意开展真正的政治变革,民众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变革,政治变革的动力因此就消失了,政治变革陷入无所进展的困境之中。不仅如此,对于民众中的某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来说,他们本应是要求进行真正政治变革的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但他们一方面忌惮当局的残酷镇压(以往的各次镇压早已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另一方面又面临当局的收买,于是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便在政治变革的问题上集体失语,不但回避政治的症结问题,甚至还美化现状。一句话,他们“犬儒化”了。当这些比普通民众具有更大影响力的精英们与当局沆瀣一气时,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强化了。
如图1-2所示,鉴于上述原因,所以近些年来在大陆不但很少有人出来主张真正的政治变革,甚至连公开指出大陆政治的症结所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政治变革又如何可能有所进展呢?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由于身在这个博弈局之外,所以虽然他们既敢于指出大陆政治的症结所在,又敢于采取直接针对中共一党专政的积极行动,但在改变中国政治变革的这个困境方面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
图1-2: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强化
二、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前景:困境的破解之道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究竟还有没有希望呢?笔者认为,大陆政治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目前这个困境能否被打破,而打破这种困境的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只是时间不可确切预知。这些可能性及其概率究竟如何呢?下面作一些分析。
要打破由博弈均衡所形成的困境,主要的突破口就在于改变博弈中的信息与博弈者的利益预期状况。就政治变革博弈来说,信息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博弈者的利益预期,主要是这个因素导致了各方博弈者作出了目前的选择,从而导致了困境状态的出现。因此,如果要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那就必须是博弈的一方或双方的利益预期都发生变化。既然这场政治博弈有两方,那么也就有两种打破困境的可能性:
首先,如果在当权者中能够出现一个甚至一批有胆有识的人,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那么这种困境就有可能被打破。这类人可能是当权者中的“异类”,他们有着和其他当权者不太一样的经历、知识结构或观念,或者不同的个性。在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方面,他们的利益预期可能不同于其他当权者,这就有可能导致他们作出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行动选择,从而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他们自己也因此成为永载青史的英雄或伟人。比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都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人物。但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太低了,尽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纵观历史,这种人终究是少数。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出现这种人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所进行的“洗脑”教育与文化宣传政策,确确实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目前的当权者恰恰是受共产党宣传教育的影响最深的一批人。同时,中国大陆的官僚体制也是一种过滤机制,一些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往往难以进入当权者的行列;即使进入了,也可能被淘汰出来,胡耀邦和赵紫阳便可以说是代表性人物。此外,即便在当权者中出现了一个或者一批这种人物,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能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那还要看他们是否具备那样的能力,包括他们的权力、资源、智慧以及行事的方法。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也无济于事。
其次,如果当权者中没有出现英雄,但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预期普遍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认识到维持现状而不推动政治变革,不再是有利的,那么,民众的行动选择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概率相当大,大陆情势的进展也支持着这样的判断。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政治的症结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大陆的腐败日盛一日,当局的苛政甚至暴政日盛一日,经济困境也日盛一日,从而使民众的生存条件逐步地恶化。比如,农村中的征地,城市中的拆迁,司法腐败,暴力压制民众上访或者示威,金融漏洞,房价暴涨,股市巨幅震荡等等,这些就是明证。不仅如此,甚至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天灾的发生,其对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作用,也会因为政治弊病的存在而被放大许多倍,亦即加剧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这些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事件及其后果表明了这一点。当民众的生存条件恶化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们就会改变利益预期,将不再认为维持现状比改变现状更好--即使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加以残酷镇压;到那时候,民众便会行动起来,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从而导致政治变革困境被打破。当然,目前这种情形尚未出现,这或许意味着,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还未普遍地达到导致他们改变利益预期的临界点。不过,考虑到民众的生存条件与政治的症结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有信心作出这样的判断:只要政治的症结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民众生存条件的普遍恶化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趋势。由此可以推论,到一定时候,临界点一定会到来,这是个或早或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历次动摇甚至推翻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运动,可以说莫不如此。
显然,在打破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两种可能性中,第一种非常小,最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只是确切时间尚不可知。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恐怕会以比较激烈甚至暴力的革命形式来进行,而不是改革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弊端会导致民众的生存条件普遍地恶化,最终导致大陆民众普遍地改变利益预期,从而改变行动选择,强烈地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再是苟活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但是目前这种情况还未发生--至少在程度上,政治现状还是有些让人觉得沮丧。然而,既然民众的生存条件的普遍恶化早晚会达到改变他们利益预期的临界点,那么,政治变革的前景就不会是令人悲观的。只是届时政治变革很可能会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来进行,则不免让人觉得可悲而可叹。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