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720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
野兽按:六四事件後隔年,中國科學家學者方勵之,以一篇《中共的遺忘術》,預言六四大屠殺將被遺忘。
25年後,一本由前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駐中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所著《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在2014年出版,試著拼起包括北京天安門、成都屠殺事件等被遺忘的歷史與視角,如試紙般在各地測試遺忘術的成果。2019年,《重返天安門》中文版在台灣發行,掀起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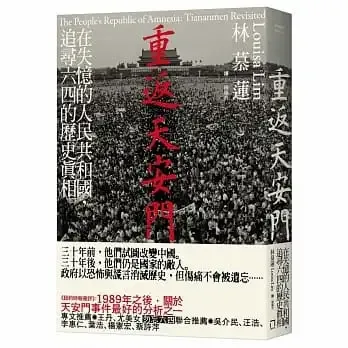
三十年前,他們懷抱熱血與夢想,試圖改變中國。
三十年後,他們仍是國家的敵人,人生支離破碎。
中共企圖以恐怖與謊言消滅真相,但曾經的暴行與傷痛不會被人們忘記。
1997年,九月,被軟禁已經長達八年的前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共高層上書,希望在21世紀結束前、迎向新世紀的關鍵時刻,針對「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實事求是,還給這群愛國學生一個公道,摘除「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項莫須有的罪名……
直到今天,又過了二十多年,六四屆滿三十週年,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不但沒有改變,反而益加蠻橫、粗暴,企圖以鋪天蓋地的手段,將這段歷史從人民的記憶中徹底抹去。封鎖新聞、竄改教科書、對異議人士人身自由的箝制、全面性的新聞與網路言論審查、在敏感日期對天安門廣場進行監控,給予服從妥協的人就業保障與升遷管道等等,種種在自由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人權侵犯,成為中國百姓的生活日常。如民運領袖王丹所言,「黑色專制」與「紅色恐怖」讓大多數人民噤若寒蟬。
本書作者林慕蓮在派駐北京的期間驚訝地發現,不僅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之一無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
「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林慕蓮
林慕蓮因此決心寫下《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在本書中,作者採訪了多位直接、間接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人物,包括學生領袖張銘、吾爾開希、奉命鎮壓清場的小兵陳光、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以及受害者家屬,包括「天安門母親」張先玲、丁子霖、成都的唐德英等人,也記錄了王丹、柴玲、劉曉波等人之事蹟或他們對六四運動的看法──他們在廣場上的親眼所見、後續的囚禁、流亡、抗爭,中國政府對他們永無寧日的監控與打壓,以及三十年來他們如何反思當年的運動、如何面對難以撫平的創痛、如何面對逐漸被社會邊緣化與遺忘,如何在國家暴力下選擇妥協,或是,如何堅定不移地持續為了平反六四而奮戰不懈……
《重返天安門》不僅只是對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回顧,更著重於挖掘1989年之後參與者的生命經驗,透過他們的人生描繪出中國政府如何有計畫、有規模地剷除任何與八九、六四、天安門有關的歷史記憶。這種集體的失憶無疑對參與者不僅不公,更是殘酷的傷害,他們曾經的奮鬥、光榮、苦痛不僅不被承認,甚至成為禁忌。然而,集體失憶對中國社會整體造成的傷害更是無法估量。在特別收錄的〈台灣版作者自序〉中林慕蓮指出,「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並讓為惡的罪犯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當一個民族拒絕正視自身的過錯與缺陷,無法檢討與反省,道德沉淪似乎就是必然的。環視今日中國的諸般社會與精神危機,否定六四、掩蓋歷史真相的危害可說是致命的。
得獎紀錄
※2014年《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2015年紐約公共圖書館海倫伯恩斯坦(Helen Bernstein Book Award)卓越新聞獎決選
※2015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Award)入圍
※《紐約時報書評》:「1989年之後,探討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最好的分析之一。」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王丹(六四民運領袖)、尤美女(立法委員)
★勿忘六四聯合推薦: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汪浩(作家、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李惠仁(導演)、葉浩(政大政治系副教授)、楊憲宏(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創會理事長)、蔡詩萍(作家、資深媒體人)
媒體好評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天安門文件》編輯):「林慕蓮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代中國人的內在不一致。在北京血腥鎮壓民主示威抗議的二十五年後,如今的中國政府繼續讓這個國家遺忘歷史,讓記得過去的人失去聲音,讓試圖探索的人無能為力。但真相從不會就此消失,只會找到新的出口。作者讓全世界重新聽到沉默目擊者的聲音,讓我們看見中國和諧表象下的潛藏夢魘。」
夏偉(Orville H.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前任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富國強兵之後》作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中以優美的筆法呈現潛心研究的成果,將失落的碎片重新拼回一九八九年的原貌,提醒我們一個無法回憶過去的國家,是如何一步步變得虛無飄渺,以假為真。」
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中國經濟季刊》與《中國經濟評論》專欄作家,《午夜北平》作者):「資深記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中以純熟的技巧,將不願沉默的聲音編織成一股抵抗的力量,帶領我們一同回到現代中國最關鍵的時刻。」
黃明珍(《神州怨》與《尋找戰友》作者):「要了解中國如何藉由散播集體失憶將自己打造成下一個經濟強權,你不能不讀這本書。」
沈彤(六四學生領袖之一,《幾乎是場革命》作者):「極為動人的一本書──思慮縝密、觀察入微、勇敢無畏。書中的人物與故事呈現出中國各種層次的面貌,並提醒著我們,這個國家為了成為新興世界強權,讓許多人稱讚可以與西方民主分庭抗禮的同時,犧牲了多少人性。」
艾明德(Adam Minter,《彭博新聞》駐上海記者、《一噸垃圾值多少錢》作者):「作者重現1989年的現場,以充滿人性的筆觸敲擊我們的心。她將歷史帶到當代人的門前,讓我們看見自己與那些倖存者以及塑造歷史和悲劇的共犯並無二致。《重返天安門》是一部完全原創的歷史著作,它將改變人們對1989年中國的理解與感受。」
《經濟學人》:「在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的二十五年之後,依然有新的細節不斷浮出水面。這位美國國家廣播電台的記者,將散落各處的碎片拼回應有的位置,讓西方的讀者以及1989年後對天安門幾乎一無所知的新一代中國人,看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作者勇敢地探索真相……筆觸充滿溫度,在具體的生命故事與整個時代的宏觀描述之間游刃有餘地切換,並在兩者之間穿插許多辛酸的小插曲」
《時代》(The Times):「林慕蓮的這本書充滿著縈繞不去的生靈之聲。他們打破沉默,重新挖出被中共官方埋藏的集體記憶。此外,作者還揭露出另一個少被注意的傷口:成都的鎮壓事件。成都的故事也許不像天安門那麼有名,但血腥程度卻不遑多讓。」
《文學評論》(The Literary Review):「這本書讓我們看見,中國用什麼方法讓十四億百姓接受了政府的思想審查。如今即使是那些在美國頂尖開明的大學留學的中國人,也沉浸於共產黨的虛假愛國主義之中,無法接受他們國家的歷史除了共產黨的官方說法之外,可能還有另一種真實。」
作者簡介
林慕蓮(Louisa Lim)
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
在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她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在北京撰寫本書期間,她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並把書稿鎖在臥室的保險箱內。除了極少數的人,無人知道她的寫作計畫。
譯者簡介
廖珮杏
輔大德語系畢業。偏好人物、文化、社會議題的書。喜歡蒐集故事,希望藉由翻譯,讓讀者看到更多各種人的樣貌。譯有《緬甸詩人的故事書》與《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譯作賜教:peixingliao@gmail.com
推薦序(一)淹沒真相,不會使歷史成為過去╱王丹
推薦序(二)史實的債越築越高,我們卻不願記憶隨之消逝╱尤美女
獻詞
天安門事件大事時間表
天安門周遭北京市地圖
照片解說
作者註
台灣版作者自序
前言
第一章 小兵──陳光
第二章 留下來的人──張銘
第三章 流亡的人──吾爾開希
第四章 學生──Feel劉
第五章 母親──張先玲、丁子霖
第六章 愛國的人──高勇
第七章 當官的人──鮑彤
第八章 成都大屠殺──唐德英
後記
謝詞
註釋
書目
第一章 小兵陳光
熊熊烈火伴隨著縷縷濃煙壟罩著整個天安門,一群士兵正把學生的物資全堆起來放火燒掉。這裡沒有一個老百姓,這個世界全都是穿著卡其布的士兵。這幫頭戴鋼盔的男人唯一的任務就是毀滅證據。他們仔細搜索被匆忙棄置的帳篷、睡袋,還有紙張。一落落的紅色長布條在地上翻動著,腥紅的顏色彷彿回應著在這之前發生的流血事件。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暴力雖然看不見,但是依然存在。
裝甲運兵車隊將槍砲口對著天安門的城門,它們就停在毛澤東主席四十年前,一九四九年站立的地方,他在此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輛一輛的坦克就排列在中國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方前面。
這些在天安門的景象,只有軍隊才看得到。學生們最終在七個星期之後,在槍口下四處散逸,逃離了廣場,那時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動員了十五萬名士兵。死傷人數至今無人知曉。中國初步統計為兩百四十一名死亡,其中二十三名為士兵。中國紅十字會最初則估計有兩千六百人死亡,這個數字基本上得到了瑞士大使的證實,他曾到訪北京的醫院,並聲稱有兩千七百人死亡。但是上述兩者皆在外交壓力下迅速撤回數字。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份美國外交電報認為,「就衝突的性質以及解放軍使用的武器來說」,這樣的數字並不合理。無論如何,這些數字都無法傳達解放軍將槍口對準自己人民時,那種全然的背叛感。
對於其中一名士兵來說,他花上好一段時間——好幾天、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才搞清楚他在當年事件中執行的任務。時至今日,當年十七歲作為隨軍攝影師在廣場上所拍下的場景,依然讓他縈迴在心。陳光現在是一位畫家,他的作品仍深受那個夜晚的經歷影響,創作了自己清楚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展示的一系列作品。那個夜晚將他的人生一分為二。他永遠無法再回復曾經的純真,或是忘掉他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同時,國家的生活也被一分為二;中國近代史在那個晚上發生了轉折——不過卻無人談論,而且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人對此一無所知。
……
陳光第一次跟我說他的故事的時候,刻意避開了那個漫長夜晚的過多細節。他只是一點一點地透露他在六月四日的任務。下一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拜訪了他的新家,位於北京東邊十六英里的一個簡樸農村宋莊,這個地方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藝術中心。
這個村子的路邊沒有農民在賣西瓜,只有藝術家蹲在塵土中,兜售拙劣的梵谷複製畫,或是用歪歪扭扭的線條繪製成的毛主席喝茶圖。藝品店已經取代了其他所有商店,在這裡購買帶有金色斑點的書法紙竟比買水果等食物要來得容易許多。各種名堂的藝術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光是從它們的名字就可見一斑,例如:捷克中國當代藝術館,國防藝術區、非洲藝術博物館。但即使是最大最閃亮的宋莊美術館,在我最近幾次的拜訪期間都空無一人,門是鎖上的,窗戶也積滿了灰塵。這些荒涼的展覽空間是中央規劃主張「只要蓋了,人就會來」的失敗證明。政府在宋莊投資一千三百萬美元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群集,吸引了大約四千名藝術家,但這些藝術目的似乎沒有帶來可行的經濟價值。
陳光的新家就藏在一個亮藍色波紋的鐵柵欄後方的一個建築工地內。這裡前景堪慮,一條黃色的泥土路,只有運貨卡車會來。不過在看不見的遠方是另一排漂亮的三層灰色磚房。雖然他無法在中國展示他的作品,不過顯然在海外的銷售成績相當不錯。因為他剛剛買了兩間相鄰的廠房工作室,有二十五英尺高的天花板和別緻的夾層陽台。他的工作室就夾在兩個建築工地之間,是一個明亮、通風的避難所,讓他遠離公寓後方十幾棟拔地而起的十六層樓房所發出的錘擊與鑽孔聲。
在工作室裡,兩幅估計有數十年畫齡價值的畫作靠在牆上,外面小心地用氣泡包裝紙保護著。它們都代表且增強他那晚的記憶。我們啜飲著綠茶,他不停地抽著菸,終於開口向我訴說他的故事。
軍隊準備採取更隱蔽方法進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輛滿載著平民服裝的卡車抵達射擊場。當局決定,下一次進入北京的任何嘗試都不會再像之前那樣失敗收場。上頭下令讓每個士兵挑選一件平民服裝來穿,好隱藏真實身分。陳光選了一件深藍色長褲和一件灰色上衣。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樣坐卡車進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鐵、公共汽車,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點就是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要在當天晚上六點之前抵達。
當時,陳光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療哮喘與腹瀉,他的上級擔心他沒有足夠的體力獨自抵達廣場,便命令他乘坐改裝的公車前往天安門廣場。當陳光看到改裝的公車時,他注意到所有的座椅都被移除,騰出地方來放一箱箱堆在窗台前的槍枝彈藥。陳光蹲坐在木板箱的旁邊,他是車上唯一的乘客。他第一個反應是鬆了一口氣,因為有便車可搭,不用怕在這個陌生的大城市裡迷路。
公車緩緩駛入北京。它只被一群學生阻擋了一次;這群學生只是敷衍地往裡頭望了一下,就放行讓它繼續往前開。當時他沒想過自己有多麼幸運。事實上,他的旅程相當順暢,他是第一批抵達人民大會堂的人之一,抵達目的地時才下午三點三十分,比約定集合的時間早了兩個小時。他受命打開車廂,將槍枝分批走私進人民大會堂。他每趟都抱著五六把衝鋒槍,到最後他的手跟衣服都被塗上了一層油脂,這些黑色油脂是在打包時保護槍枝用的。當他把槍搬運到寬敞的中庭時,便看到那裡擠滿了正在找尋自己小隊的便衣士兵。他們一找到自己的小隊,就會拿到各種顏色的布條,用以區別不同的部隊。直到可以穿回制服之前,士兵們都要將布條別在手臂上。陳光曾在電視新聞上看過人民大會堂,畫面是一排排坐得整整齊齊的代表,一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年度會議上彬彬有禮地拍手致意。所以當他見到這個神聖的地方竟擠滿了武裝的士兵時,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從某個縫隙掉進一個無法理解的世界。
下午六點左右,已換回制服的陳光的部隊被賦予了新的任務。他們受命去搶救罪犯從車上偷走的軍火彈藥,那一輛公車被扣押在電信大樓附近,靠近長安街西單十字路口。他回憶,「我當時才感覺到很可怕。」那時他突然得知,一名跟他一樣負責護送武器的士兵,在進入北京市中心時被人發現了。
翌日他聽說,在六月四日的清晨,一位名叫劉國庚的二十五歲士兵在取槍地點附近被一群暴徒謀殺。中國國營媒體把他的屍體當成一個宣傳圖像,用來描繪戒嚴部隊碰上了危險;劉焦黑的屍體被吊著脖子掛在一輛發黑的公車上,他全身赤裸只著襪子,頭上則帶著一頂未被燒毀的鋼盔。他立刻被追封成烈士。電視新聞播出國家領導人安慰著他家中哭泣的父親的畫面。
官方報導指出,示威群眾在長安街口攔截一些載著彈藥準備前往後方支援的車輛,劉的部隊也被包圍。當劉發現問題的時候,他折返回來想要幫助他的小隊。關於這段歷史,官方批准的版本發表在一本名為《北京風波紀實》的書中,書中內容稱:「一群暴徒猛撲過來,磚頭、瓶子、鐵棍雨點般地打在他倆的頭部、胸部,司機當場被打昏,劉國庚被暴徒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後,又被暴徒焚燒,並將遺體吊在一輛大轎車上。此後,一名喪心病狂的暴徒又將烈士遺體剖腹」這是兇殺案發生不久之後,一個相當惡劣的宣傳計畫的一部份,這段時間政府試圖用官方版本來蒙蔽整個國家。
街頭巷尾流傳的是另一個說法,劉用他的AK47殺害了四個人,然後在他彈藥耗盡的時候被處以私刑。事實上,他被吊在公車上的照片被人刻意截去了一部分。那輛滿是塵土的公車側面,其實還潦草寫著幾句標語:「他殺死四人!殺人犯!人民必勝!血債血還!」而看見一副士兵的屍體被吊在與他用來運送武器的同樣的公車上,對陳光來說有著天翻地覆的意義。「他和我一樣也是押送槍支彈藥的。」他相當篤定地告訴我,不在乎這之間的差異。
六月三日晚上,陳光的部隊在接到奪回武器的命令之後,從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後門出去,結果又被激憤的群眾用人海戰術對付。陳光與他的部隊被包圍得動彈不得。示威群眾除了繼續對他們說教,還做了一些別的事,「不知道從哪兒飛來的磚頭、酒瓶子砸到我們頭上。有的當兵的被砸的滿臉是血。我們這些軍人互相抱地很嚴實,你抱著我我抱著你,頭挨著頭。那些磚頭和酒瓶子就從我們的頭盔上滾出去了。」
部隊沒有接到下一道指令,所以他們只能盤腿坐在大廳外面。有段時間,他們甚至唱起歌來對抗包圍他們的人,這個滑稽的競賽可能多少讓學生們產生錯誤的安全感。士兵們拉開嗓子大唱軍歌,試圖蓋過學生們演唱的共產主義國歌《國際歌》。大約三個半小時之後,約莫九點半左右,士兵接到命令退回人民大會堂內部。當全員在裡頭等待的時候,不時有磚塊砸上窗戶。
然後一段高壓的緊張局勢開始。戒嚴部隊在通往廣場的大門後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時分,彈藥已經分發下來,每個人四條彈匣,每條彈匣有五十到六十發子彈,一條上膛,另外三條掛在他們的胸前。「當然害怕了。」陳光說,一邊又倒了一杯散發清香的綠茶,手在發抖。「沒有子彈的時候你拿著那個槍,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甚至還沒有拿把菜刀危險。但是你要壓上子彈了,就很危險了。」
氣氛相當緊張,常常發生擦槍走火的意外,子彈射穿大廳的天花板。「從九點半我們回來進去之後,他們又馬上說要去廣場。從九點、十點、十一點,到十二點,一直說要出去。但我們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哪兒,抱著槍,一直在那兒等。」
陳光已經等到失去時間概念,門突然被打開了。命令下來說要清理廣場。當他跟著他的小隊站在人民大會堂前的階梯上時,允許開槍的消息一排一排傳了過來。「那時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軍人告訴後面的軍人說,如果遇到危險的情況,可以開槍。說上面有命令。就是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這麼說的。」
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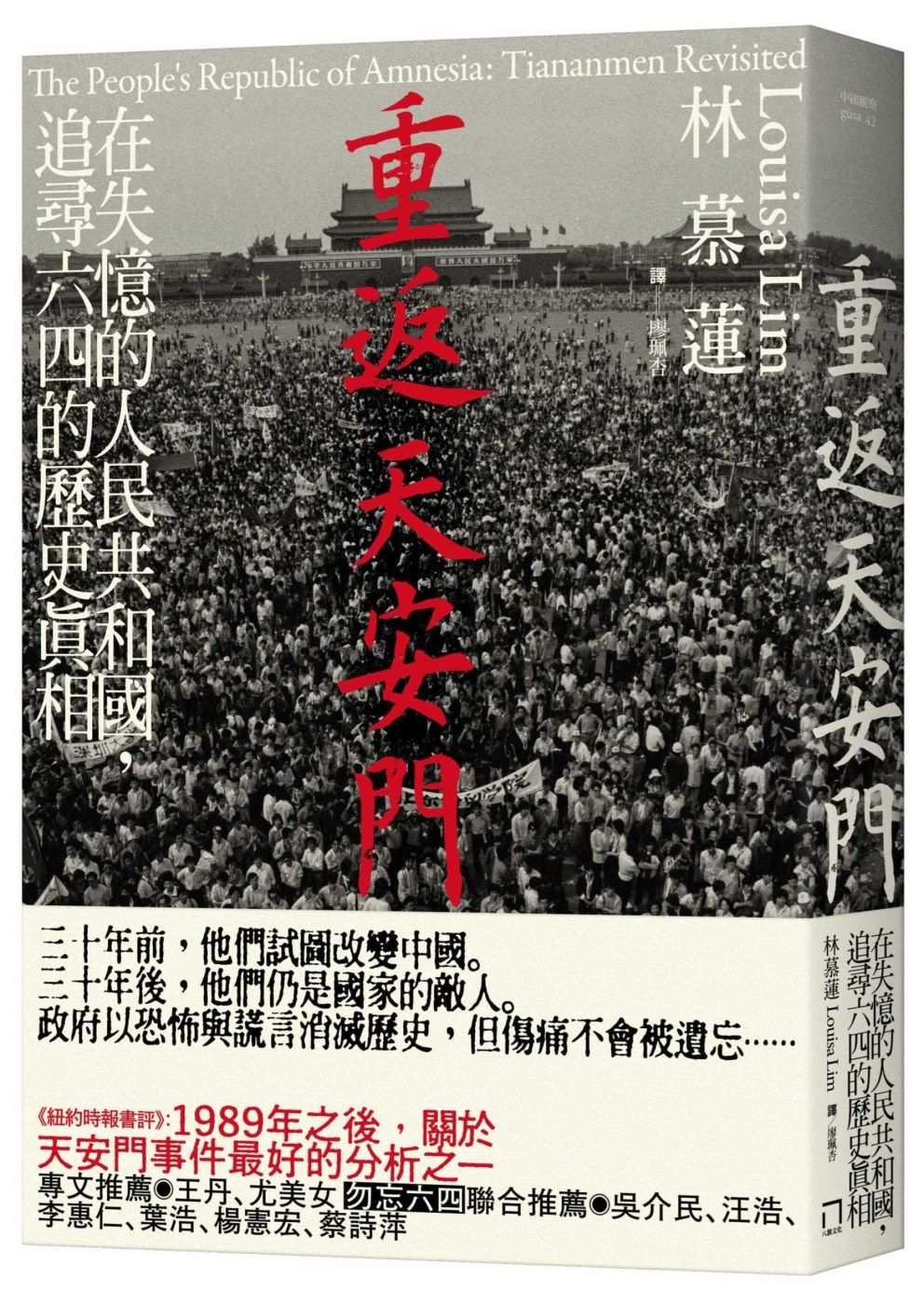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上網路;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也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
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是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仍然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顯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的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30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祕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